撰文/周程(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醫(yī)學(xué)人文學(xué)院院長)
編輯/吉菁菁 校對/李云鳳 供圖/視覺中國
雖然重視知識生產(chǎn)勝過知識傳播的辦學(xué)模式 曾引起日本民眾的非議,但它在創(chuàng)新型人才 的選拔和培養(yǎng)上確實(shí)存在諸多優(yōu)勢。
北京時(shí)間10月9日傍晚,2019年諾貝爾化學(xué)獎(jiǎng)評審結(jié)果揭曉。日本旭化成工業(yè)株式會(huì)社名譽(yù)研究員、名城大學(xué)教授吉野彰博士因率先研制出可充電的現(xiàn)代高性能鋰離子電池與其他兩位美國科學(xué)家共享本年度諾貝爾化學(xué)獎(jiǎng)。至此,日本已有24人榮獲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除湯川秀樹、朝永振一郎、江崎玲于奈、福井謙一、利根川進(jìn)5人外,其他19人都是在進(jìn)入新世紀(jì)后獲得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的。雖然其中的兩位物理學(xué)獎(jiǎng)得主——南部陽一郎和中村修二獲獎(jiǎng)時(shí)已加入美國籍,但他們的獲獎(jiǎng)成果都是在加入美國籍之前做出的。

▲日本旭化成工業(yè)株式會(huì)社名譽(yù)研究員、名城大學(xué)教授吉野彰(Akira Yoshino)與其他兩位美國科學(xué)家共享2019年度諾貝爾化學(xué)獎(jiǎng)后,日本榮獲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的人數(shù)已攀升至24人。
日本進(jìn)入新世紀(jì)后,幾近平均每年獲得1枚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獎(jiǎng)牌,獲獎(jiǎng)總?cè)藬?shù)僅次于美國,將過去的諾貝爾獎(jiǎng)強(qiáng)國——英國、德國、法國遠(yuǎn)遠(yuǎn)甩在身后,令國際社會(huì)感嘆不已。日本何以在21世紀(jì)最初二十年出現(xiàn)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井噴”現(xiàn)象?
日本新世紀(jì)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分析
日本新世紀(jì)19名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中,出生在二戰(zhàn)結(jié)束之前的有13人。其中,出生在1926-1935年間和1936-1945年間的各占6人,另外一人是南部陽一郎,他出生于1921年。戰(zhàn)后出生的6人中,有2人出生于1946-1955年間,另外4人則出生于1956-1965年間。換言之,日本新世紀(jì)19名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中,2/3以上出生在戰(zhàn)敗前。日本新世紀(jì)19名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的出生年平均值約為1942。如果按照年代進(jìn)行統(tǒng)計(jì),詳見圖1。
日本新世紀(jì)19名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中,有16人的獲獎(jiǎng)奠基性成果是在上個(gè)世紀(jì)七、八、九十年代做出的。其中,有7人的獲獎(jiǎng)成果是在1970年代做出的,在1980年代做出獲獎(jiǎng)成果的有5人,在1990年代做出獲獎(jiǎng)成果的有4人。剩余3人中,南部陽一郎和下村修的獲獎(jiǎng)成果是在1960年代做出的,而且都是在美國工作期間做出的。另外1人是山中伸彌,他的獲獎(jiǎng)成果是在21世紀(jì)初做出的。參見圖2。簡言之,八成以上的日本新世紀(jì)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都是在上個(gè)世紀(jì)最后30年間做出獲獎(jiǎng)奠基性成果的。
除去南部陽一郎,所有的日本新世紀(jì)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都是在戰(zhàn)后接受高等教育的。而且,日本新世紀(jì)獲獎(jiǎng)?wù)咧校挥幸蝗顺錾碛谌毡舅搅⒋髮W(xué),在國立綜合大學(xué)——名古屋大學(xué)、京都大學(xué)、東京大學(xué)讀本科或取得博士學(xué)位的獲獎(jiǎng)人數(shù)最多,均在4人以上。目前,在由原帝國大學(xué)改造而成的7所國立綜合大學(xué)中,除九州大學(xué)外,都至少培養(yǎng)出了1名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
至此,我們可以大致構(gòu)建出這樣的圖景:
日本新世紀(jì)19名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絕大多數(shù)出生在二戰(zhàn)結(jié)束前;他們幾乎都是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進(jìn)入中學(xué)或國立大學(xué)讀書的;而且大多是在1964年日本舉辦東京奧運(yùn)會(huì)前后進(jìn)入國立綜合大學(xué)研究生院學(xué)習(xí)的;1968年日本經(jīng)濟(jì)總量超越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之后,他們開始進(jìn)入或正在著名大學(xué)或骨干企業(yè)從事科學(xué)研究;進(jìn)入1970年代,他們陸續(xù)取得重大研究突破,從而為新世紀(jì)榮獲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奠定了基礎(chǔ)。

▲圖1日本新世紀(jì)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出生年代分布圖

▲圖2 日本新世紀(jì)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做出獲獎(jiǎng)奠基性成果時(shí)的年齡分布圖
日本新世紀(jì)高產(chǎn)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與戰(zhàn)后的教育改革關(guān)聯(lián)甚大
日本新世紀(jì)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幾乎都是在戰(zhàn)后接受中學(xué)和/或大學(xué)教育的。當(dāng)時(shí)日本的教育正經(jīng)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
1926年進(jìn)入昭和時(shí)代之后不久,日本便進(jìn)入了動(dòng)蕩不安的軍國主義黑暗時(shí)期。這一時(shí)期,日本的教育旨在讓個(gè)人無條件地服從國家,這明顯與啟蒙主義教育理念相悖。為了給軍國主義搖旗吶喊,日本的媒體開始大肆渲染本國的軍事、科技乃至社會(huì)優(yōu)勢。當(dāng)時(shí)被廣泛閱讀的兩本科普雜志——1923年創(chuàng)刊的《科學(xué)畫報(bào)》 和1924年創(chuàng)刊的《兒童科學(xué)》在軍國主義者的操控下幾乎每期都在鼓吹日本的軍事優(yōu)勢和科技成就,以致日本青少年都想從軍,以為日本可以稱雄世界。1939年的諾門罕戰(zhàn)役使日本有識之士意識到日本不能再自欺欺人了,必須進(jìn)行教育改革。但是,走上了軍事擴(kuò)張不歸路的日本在二戰(zhàn)期間是不可能對教育進(jìn)行民主主義改革的。
戰(zhàn)后,在美國的推動(dòng)下,日本于1947年頒布了《教育基本法》,開始用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教育取代以往的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教育。東京、京都、東北、北海道、九州、大阪、名古屋等七所帝國大學(xué)正是在這一時(shí)期被改造成為國立綜合大學(xué)的。雖然它們都叫做國立大學(xué),但實(shí)際上享有高度的自主權(quán)。戰(zhàn)后初期的教育改革不僅使日本的大學(xué)教師獲得了更多的研究自由和穩(wěn)定的經(jīng)費(fèi)支撐,而且還使學(xué)生獲得了更多的參與科學(xué)研究的機(jī)會(huì),得到了更多的科學(xué)研究訓(xùn)練。這些無疑會(huì)對戰(zhàn)后入學(xué)的青年學(xué)子的科學(xué)研究產(chǎn)生積極影響。
1992年、2007年的卡內(nèi)基大學(xué)教師國際調(diào)查顯示,七成左右的日本大學(xué)教師在教學(xué)與科研中更重視后者。在國立綜合大學(xué),這種“科研至上”的風(fēng)氣更濃。雖然重視知識生產(chǎn)勝過知識傳播的辦學(xué)模式曾引起日本民眾的非議,但它在創(chuàng)新型人才的選拔和培養(yǎng)上確實(shí)存在諸多優(yōu)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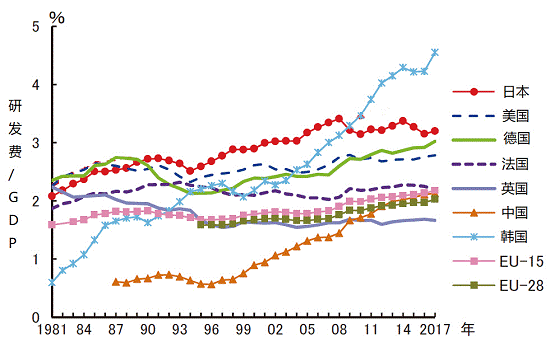
▲圖 3 主要國家研發(fā)經(jīng)費(fèi)投入強(qiáng)度變化趨勢圖
日本新世紀(jì)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深受導(dǎo)師熱衷科研的影響
上個(gè)世紀(jì)五六十年代在日本國立綜合大學(xué)指導(dǎo)學(xué)生開展研究的教師都經(jīng)歷過戰(zhàn)時(shí)研究。戰(zhàn)時(shí),在軍工需求的拉動(dòng)下,他們不得不夜以繼日地高強(qiáng)度工作。特別是在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為了挽回?cái)【郑麄兇蠖嘀苯踊蜷g接地參與了與武器開發(fā)和生產(chǎn)有關(guān)的研究。目睹技不如人的日本被科技強(qiáng)國美國占領(lǐng),他們比誰都更加清楚攀登科學(xué)高峰、搶占技術(shù)制高點(diǎn)的重要性。
1952年,舊金山和約簽署之后,美國結(jié)束了對日本的占領(lǐng)。經(jīng)受過戰(zhàn)爭磨練的這些大學(xué)教師,擁有充分的研究自由后,為迅速提升日本的科技競爭力,在爭分奪秒地開展科學(xué)研究的同時(shí),還盡其所能地指導(dǎo)著自己的學(xué)生。
由于日本新世紀(jì)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在大學(xué)讀書時(shí)的導(dǎo)師大多經(jīng)歷過二戰(zhàn),對科技競爭的殘酷性和重要性有著深切的感悟,因此人人都可以說是拼命三郎,而且對科研選題的新穎性和科研數(shù)據(jù)的準(zhǔn)確性要求極嚴(yán)。這種精神氣質(zhì)當(dāng)然會(huì)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傳遞給他們的弟子。他們的弟子在其耳提面命之下,對日本走技術(shù)立國的道路、迅速提升科技水平的必要性也有著與今日的“寬松世代”不同的理解,并且都甘愿為日本的科技發(fā)展不懈努力。
1964年,東京奧運(yùn)會(huì)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日本的科技實(shí)力;1965年,朝永振一郎又繼湯川秀樹之后再度摘得諾貝爾物理學(xué)獎(jiǎng)。這些成功使日本新世紀(jì)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的導(dǎo)師們迅速恢復(fù)了自信,同時(shí)也極大地提振了他們弟子的科技自信心。這些青年學(xué)子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只要自己勤奮努力、勇于攻堅(jiān)克難,就有可能做出世界一流的科技貢獻(xiàn)。因此,他們不愿意再繼續(xù)跟蹤模仿西方,而是瞄準(zhǔn)世界科技前沿大膽地向無人區(qū)挺進(jìn)。如果他們當(dāng)時(shí)不敢挑戰(zhàn)世界科技難題,很難想象他們之后能取得那么多令世人矚目的科技成就。
日本新世紀(jì)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得益于研發(fā)經(jīng)費(fèi)的持續(xù)增長
搞科研只有主觀愿望不行,還得有先進(jìn)的儀器設(shè)備和充裕的研究經(jīng)費(fèi),這些都需要有堅(jiān)實(shí)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支撐。幸運(yùn)的是,日本新世紀(jì)諾貝爾獎(jiǎng)得主投身科研領(lǐng)域時(shí),正好遇上了日本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期。
上個(gè)世紀(jì)六十年代,日本在大多數(shù)年份都保持了兩位數(shù)的經(jīng)濟(jì)增長率。結(jié)果,日本的經(jīng)濟(jì)增長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國民收入倍增計(jì)劃”1960年定下的在今后10年中將國民生產(chǎn)總值提高2倍以上的目標(biāo)。日本在制訂“國民收入倍增計(jì)劃”的同時(shí),還制定了與此目標(biāo)相呼應(yīng)的“振興科學(xué)技術(shù)的綜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爭將國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這一數(shù)值目標(biāo)進(jìn)入七十年代后不久即告達(dá)成,也就是說,日本上個(gè)世紀(jì)七十年代初的研發(fā)經(jīng)費(fèi)投入強(qiáng)度就達(dá)到了我國今天的水準(zhǔn)。
上個(gè)世紀(jì)七十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jī)對世界經(jīng)濟(jì)造成了很大的沖擊,但在節(jié)能環(huán)保等產(chǎn)業(yè)的帶動(dòng)下,日本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這一時(shí)期仍然增長了1.8倍。伴隨著經(jīng)濟(jì)的高速增長,日本的研發(fā)經(jīng)費(fèi)投入也在不斷攀升。1975年,日本的研發(fā)經(jīng)費(fèi)總額達(dá)到了2.62萬億日元,占國民收入的2.11%,超過了法、英兩國的研發(fā)經(jīng)費(fèi)總和。
在上個(gè)世紀(jì)最后的20年里,除去泡沫經(jīng)濟(jì)破裂之初的三四年,日本的研發(fā)經(jīng)費(fèi)投入與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之比仍然呈不斷攀升的態(tài)勢。至上個(gè)世紀(jì)末,日本的研發(fā)經(jīng)費(fèi)投入強(qiáng)度直逼3%,甩開美國、德國至少0.3個(gè)百分點(diǎn)。參見圖3。
前已述及,日本新世紀(jì)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的獲獎(jiǎng)研究成果幾乎都是在進(jìn)入1970年代之后取得的。這意味著日本新世紀(jì)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得主大多數(shù)是在日本將研發(fā)經(jīng)費(fèi)投入占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之比提高到2%之后才取得重大科技突破的。這一點(diǎn)非常重要!沒有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強(qiáng)有力支撐,也許能夠偶然做出一兩項(xiàng)諾貝爾獎(jiǎng)級的科學(xué)貢獻(xiàn),但出現(xiàn)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井噴”,一定離不開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強(qiáng)有力支撐。
結(jié)語
討論日本新世紀(jì)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井噴”現(xiàn)象,不能不觸及日本政府2001年提出的在21世紀(jì)前50年里獲30個(gè)諾貝爾獎(jiǎng)之計(jì)劃。當(dāng)時(shí),不少學(xué)者著文對這一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表示了擔(dān)憂。然而,在今天,大多數(shù)人已經(jīng)不會(huì)再去懷疑這一點(diǎn)。原因無他,在過去二十年里,這個(gè)計(jì)劃展示了驚人的完成度!
雖然多數(shù)人當(dāng)下對這一計(jì)劃的完成都持有信心,但仍有人認(rèn)為日本頻繁斬獲諾貝爾獎(jiǎng)的好日子即將到頭。有報(bào)道指出,日本近年來穩(wěn)定支撐研究經(jīng)費(fèi)遭到削減,科研人員需要花更多的時(shí)間去填寫項(xiàng)目申請書;而且,研究環(huán)境的惡化已導(dǎo)致國際論文數(shù)量和質(zhì)量的下降。
盡管日本的“寬松世代”因貪圖安逸越來越不愿意出國留學(xué),大學(xué)行政法人化迫使部分教師不得不由基礎(chǔ)研究轉(zhuǎn)向應(yīng)用研究,但是,日本的研發(fā)經(jīng)費(fèi)投入強(qiáng)度仍高于3.0%,教育體制和科技體制的運(yùn)轉(zhuǎn)仍屬正常,而且科研人員的價(jià)值取向和精神狀態(tài)并沒有發(fā)生明顯的變化。因此,有理由相信,日本的50年30個(gè)諾貝爾獎(jiǎng)計(jì)劃完全有可能順利完成,只是日本的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井噴”有可能隨著二戰(zhàn)結(jié)束前出生的科學(xué)家的退出而逐漸減弱。還有,當(dāng)中國躋身于世界科技強(qiáng)國行列之后,很有可能會(huì)奪走更多的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以致日本的諾貝爾科學(xué)獎(jiǎng)“井噴”難以為繼。■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微博
科普中國微博

 幫助
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