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駿對中國動畫的失望無以復加,我也如此。“
2014年,面對中國記者的采訪,日本著名動畫公司吉卜力的核心人物、宮崎駿的合伙人高畑勛緩緩說道。

1984年,《風之谷》制作完成,作為獎勵,擔任宮崎駿《風之谷》制片的高畑勛跟宮崎駿一同前往中國旅行。
當時的中國正改革開放,新鮮的事物充斥著這片古老的大地。
西服成為北京的流行服裝,而高畑勛、宮崎駿一行卻穿著夾克,顯得格格不入。進入酒店時,里面的客人把他們當成服務員,朝他們做出了“噓”的手勢。
從那以后,宮崎駿再也沒有穿過夾克。

這個小插曲,并沒有影響宮崎駿的心情,北京只是第一站,對他來說,更重要的一站是上海。
可以說,這是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溯源之旅。
事實上,這不是日本動畫大師第一次到上海溯源。
在四年以前,另一位日本動畫大師,阿童木的創作者手冢治蟲也在北京匆匆過站,直接奔向了上海。

目的地是上海美術制片廠,對他來說,那一個神秘而充滿魔力的地方,那是一個圓三十年夢的地方。
三十八年前,當時只有十四歲的手冢治蟲在電影院里看到了亞洲第一部有聲動畫長片《鐵扇公主》。


看完之后,他驚為神作,并從此改變成了自己的理想,從當一名醫生變成一名動畫師。
“當時我還在讀初中,也有幸觀看了這部動畫電影,影片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這就是我們的動畫片啊!影片上映時盛況空前,連影院的走廊都擠滿了觀眾,場場爆滿……大人、小孩,外行的、內行的都入迷地觀看電影,這就是我想做動畫片的原因。”
事實上,手冢治蟲看的還是一部搶來的動畫片。
這部動畫片出自中國動畫大師萬籟鳴之手。

萬籟鳴原本是上海商務印書的一名美工,因為受到美國動畫的啟發,決定做出中國的動畫,從皮影等中國技藝中他獲取靈感,開始創作出了中國一部部開創性的作品。

到1941年,萬籟鳴創作出了中國也是亞洲第一部有聲動畫長片《鐵扇公主》,可剛上映,日軍侵略上海,拿走了《鐵扇公主》的拷貝當”戰利品“帶到日本播放。

沒想到,《鐵扇公主》一播出就引起轟動,用萬人空巷來形容也不為過。
時到今日,日本的動漫中依然有《鐵扇公主》留下的痕跡。
《火影里》六道仙人所留下的忍具就是芭蕉扇。

龜仙人同樣有芭蕉扇。

而手冢治蟲還看出了隱藏在動畫背后的深意。
“抱著輕視的眼光去看中國第一部動畫(長)片的人們,看到這部影片如此豪華,如此有趣,驚得目瞪口呆。我也有機會弄到了一部影片拷貝,一看就能清楚,地地道道,這是一個體現反抗精神的作品,粗暴地蹂躪中國的日本軍遭到了中國人民齊心協力的痛擊,這部影片的意圖是一清二楚的。”
在《鐵扇公主》的影響下,手冢治蟲走上了動畫的道路,最終成為了日本的動畫大師。
在他的《阿童木》引進了央視后,他趁機到中國旅游,在北京短暫停留后直奔上海。
跟宮崎駿失望之旅不同的是,手冢治蟲的上海之旅相當滿足。他不僅見到了啟迪他的中國動畫大師萬籟鳴,還一起觀看了萬籟鳴更多的作品。

當然不得不提那部至今讓人驚嘆不已的《大鬧天宮》

六十多年后,有人在外網上傳了《大鬧天宮》的視頻,頓時引來了無數人的點贊。

“當我看這個電影的時候,還是個小女孩。那時候英國4頻道開播,它開始播的那些節目中有一個就是這個電影。我后來再也沒有看過它,我曾經懷疑了很長的時間,它是否只是我曾經做過的某個好到難以相信的奇異瑰麗的夢境。現在再看到它,它就象我曾經記憶的那樣華麗壯觀。太謝謝你上傳了!”

“我自從七八歲以后就沒有看過這個電影,BBC2曾經有一季亞洲動畫。試圖獲得這個電影有許多年了,它讓我保持安靜了45分鐘”

“上帝啊,這是1960年代制作的動畫片,那時候動畫甚至還沒有那么發達。嗯嗯嗯,而且它是中國制作的還不是日本。”

在上海美術制片廠,手冢治蟲畫下了阿童木跟孫悟空握手的漫畫。

回國后,他創作的最后一部動畫就叫《我是孫悟空》,在創作《我是孫悟空》時伏案逝世,留下遺言:我已經成為孫悟空了。
宮崎駿也是帶著崇敬和期待的心情開啟了自己的上海之旅。
同樣,他也是來追溯自己的動畫生涯的起源。
將宮崎駿帶上動畫道路的是東映公司的第一部彩色動畫片,片名為《白蛇傳》。

“我得很慚愧地承認,我愛上了女性英雄主義的動畫。我被深深的震撼了,大雪中,我跌跌撞撞的走回家中。與他們(劇中人物)的執著比起來,我為自己感到非常地羞愧,哭了一整個晚上。”
彼時,宮崎駿在大學就讀的是政治經濟學院。可在看過白素貞之后,他對這位中國的神話人物著了迷,他就此改行做了一名動漫師,并在畢業之后成功進了《白蛇傳》的制作公司東映公司。
也許,他想看看中國的動畫是如何描繪中國的神話故事。
旅程以驚艷開始。
“ 在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創作了許多優秀作品。其中特偉先生的水墨動畫片,讓我們驚嘆不已。可以說,我們那些留白較多的作品正是受到了他的影響。有一些日本電影人在二戰后留在中國,參與新中國的電影制作,其中,持永只仁先生做了很大的貢獻,他和特偉先生一起參與創立了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我真心覺得這值得驕傲。”
“比起《牧笛》,特偉先生早期的《小蝌蚪找媽媽》,看的時候我都傻了,沒想到竟然能做出這樣的作品。”

二十八年后,當高畑勛談起那次訪問,依然驚嘆不已。
可接下來的事情讓宮崎駿感到有些尷尬。
宮崎駿向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贈送了《風之谷》的膠片,希望做一些業務上的探討,但上海美術制片廠問的最多的是分配問題,尤其是詢問計件工資的可行性。
之前的上海美術制片廠是國營單位,現在改革開放重新調整,不能所有人都是統一工資。上海美術院想到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應該有這方面的經驗可以傳授一下。
高畑勛說道:“宮崎駿對中國的失望無以復加。我在這一點上也是如此。因為我們對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是很尊敬的,沒想到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高層卻只關心這個。一旦計件付酬,就再也拍不出中國學派的影片了。計件付酬不鼓勵創新—不斷投入新的短片很費錢,而系列片只要搞好開頭的部分,角色和背景定下來以后就不會花太多功夫。之前中國同行那種每一部短片都嘗試新手段的創作方式,在日本就是完全行不通的。我必須要提醒他們,中國有懂行的人。但是中國一下迎來了現代化,現在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都已經沒有原來的風格了吧。太讓人失望了。我太失望了。”
事實上,當時的吉卜力也是采用計件工資,但后面,他們回到了職員固定薪酬制。

也許是藝術領域的創作,是無法按張計算的,按計只能產生流水線的作品,而無法產生偉大的作品。
讓世界驚艷的上海美術制片廠的動畫就是在完全不考慮成本,不考慮收益的情況下制作出來的。

在當時萬元戶還是土豪的年代,上影廠實行統購統銷,獲得的收入就達百萬。這足以支持藝術家們潛心創作。
以《大鬧天宮》為例。
當時沒有計算機,也沒有3D建模技術,所有的畫面都需要畫師人工完成。
孫悟空與哪吒的戰斗,孫悟空拔出三根毫毛變出三個分身,連同真身四個攻擊哪吒,光這一個鏡頭,只有五秒鐘,卻要畫一百多張畫稿。

共畫了十幾萬張手稿,時間花去了兩年。

而為了畫好每一個動作,所有的畫師先去看京劇學動作,而畫仙女的畫師則要求先學跳舞。
為了塑造“孫悟空”的形象,萬籟鳴專程帶領劇組去北京,先是找北京各地的廟宇,觀察神態各異的神像。
里面的仙女便來自敦煌飛天的靈感。

又特地拜訪了“南猴王”鄭法祥,為“孫大圣”設計動作。

還專門邀請中央美院的張光宇教授一起來為孫悟空設計造型,
張光宇是設計屆的大牛人,中國裝飾藝術之父,也是中國現代藝術的奠基人。
陳丹青說道:”真的現代藝術,真的前衛,有過么?有過,但視而不見,那就是光宇先生八十多年前做的事“

在四十年代時,張光宇先生就制造過孫悟空的形象,這一次算是重操舊業。
為了設計孫悟空的形象,張光宇數易其稿,最初是偏丑角的猴子。

雖然臉不太對,但雞心形的面部裝飾、大耳朵、帽子、以及最關鍵的豹皮裙留了下來。

第二稿,孫悟空頭戴雞毛帽,披竹盔甲,生動活沷,大王派十足,但太過復雜,不合適做動畫。

第三稿,做簡化,但造型有點方,沒有了靈氣。
連做三稿都不成功,張光宇也有些著急了:主角孫悟空的造型,我被他難住了,一時不能脫化,你們究竟做了最后決定沒有。

最終,上影的首席動畫師嚴定憲根據張光宇先生的三稿綜合出了孫悟空的最終形象:臉似蟠桃,紅雞心,綠眉毛。鵝黃上衣,翠綠圍巾,豹皮短裙,紅褲黑靴。

這一形象,成為孫悟空最為經典的形象,就是戲說不是胡說改編不是亂編的六六老師也沒有脫離這個形象。
現在有很多人感慨,為什么我們現在拍不出《大鬧天宮》,原因之一,就是當年的制作就是為了制作一件藝術品,從來沒有考慮任何的市場因素。
這才有了不計成本的投入。
1964年,《大鬧天宮》制作完成,一出世就震驚了世人,屢獲大獎。





現在的孩子提起動漫,不是日本火影海賊王,就是美國漫威,他們并不知道,中國的動畫要早于日本,中國動畫的黃金時代,成就更在日本動漫之上。
因為那些作品都是按照藝術品去打磨的。
《小蝌蚪找媽媽》,水墨畫動畫,流動的齊白石。

《聰明的鴨子》第一部折紙片

第一部彩色寬熒幕動畫長片《哪吒鬧海》。今年大熱的魔童哪咤也很不錯,但我必須得說,那是成功的商業片,而這個是藝術。



黑貓警長

《葫蘆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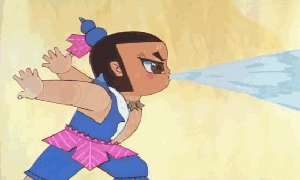
《阿凡提的故事》

《天書奇譚》

《九色鹿》

《邋遢大王》

《舒克和貝塔》

1999年,上海美術制片廠第一部市場化的動畫片《寶蓮燈》上映,當時以為是中國動畫的新開始,卻沒想到是一個結束。

自此之后,上海美術制片廠再也沒有出過匹配藝術兩個字的作品。
在那之后 ,中國的孩子只能看《喜羊羊》《熊出沒》這些剛過及格線的作品,更不用提什么洛洛歷險記,蔬菜寶寶,以及一堆動畫扶助政策下出來的奇怪動畫片。
中國現在的動畫缺了什么?
也許是匠心兩個字。
今年大火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已經讓人眼前一亮,但只能說它是成功的商業片,而不能說是藝術。
1979年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制作的《哪吒鬧海》可以說是一種藝術。

里面的服裝設計富有中國風,畫面融入壁畫和水墨元素。

配樂,更是集民樂交響的于一體——嗩吶、竹笛、笙、簫、琵琶、揚琴、箏、阮、傳統打擊樂齊齊亮相。其中的龍宮部分,據說直接使用了剛剛出土的曾侯乙編鐘(鎮國之寶啊)
哪吒鬧海的美術設計張仃先生,還是當年國徽的設計者之一。

而李靖撫琴堪稱神片段。

在長達40秒的李靖彈奏古琴的畫面,音畫神同步,雙手指法、按壓位置完全還原,連神態做到了神還原。

為了達到這種效果,《哪吒鬧海》的作曲家金復載邀請自己的好友古琴演奏家龔一到美影廠演奏琴曲。

然后六位動畫家圍繞龔一,從不同角度速寫龔一的指法。同時,還用攝影機拍下龔一演奏時的神態。
經過這樣的努力,才達到了這樣的神還原。

其實,就算指法不吻合,百分之九十九的觀眾也看不出來。隨便畫一下,就能省去不少時間跟金錢,但他們依然大費周章去做,倒不是為了能看出來的百分之一的觀眾。而是他們認為,這是藝術,藝術就得用真的態度去創作。
想想現在的演員,連臺詞都不背,全靠對嘴型,嘴型對不上,就靠切。完全不是一個級別的創作態度,反而能拿數千萬一年的片酬。
也許,上海美術的這些創作是一個無法復制無法重來的巔峰。
這樣的經典將永恒的留在我們的記憶里,留在美術以及動畫創作史上。
如果可以,應該將這樣的美,這樣的經典傳給我們的孩子。這些藝術品級的作品都是大師不惜成本制作出來的,這是不可復制的神作。因為當藝術走向市場,走向功利時,藝術就會變成另一個樣子。
蔣柳,文史作家,歷史自媒體“腦洞歷史觀”主筆,頭條學院講師,國學文化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倡導打開腦洞看歷史。著有《讀懂春秋,就懂了當下》《諸王的游戲》《隋唐不演義》《唐末刀鋒匯》等。其自媒體“腦洞歷史觀”,擁有百萬訂閱,閱讀達二十億人次。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微博
科普中國微博

 幫助
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