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一款名為“藍鯨”的自殺游戲風靡俄羅斯的網絡。該游戲以任務的形式誘導心智尚不穩定的青少年內心的陰暗情緒(如輕階任務“一天不跟任何人說話”、“4:30起床看恐怖電影”,“升級”至重階則為自殘),而將其一步步推向自愿自殺。這個新聞不禁讓人唏噓,人的心理世界并不是可以單標簽化的,悲觀與樂觀如影隨形,一步一步逐漸被引導走向、埋溺在黑暗的那一面,而后結束年輕的生命,這并不是我們所想看到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說,人類的夢是“通往無意識的大道”。夢境,一個與“意識”與“暗示”聯系在一起的看似無公害的名詞,近日在研究中卻與傾向自殺的程度聯系在了一起。
 據悉,在美國,每年有超過4.4萬人自殺身亡,自殺已成為15歲至34歲人群的第二大殺手。統計數據顯示,有多達23%的青少年有過自殘行為。過去幾個月,多項研究將噩夢與更高的自殺傾向聯系在一起。8月2日,《紐約雜志》發表加拿大住院醫生和流行病學家阿米塔·卡萊查德蘭的一篇文章,講述噩夢與自殺傾向之間的關系。全文如下:噩夢已成第二大殺手“我接觸的第一位青少年自殘患者是一名16歲的醫科學生。她留著長長的褐色頭發,身穿長袖法蘭絨襯衫。她這身打扮讓我覺得有些怪異,我記得當時是7月中旬,但她卻穿著很厚的衣服,來到我的診所。等到她挽起袖子的時候,我才知道她這么穿的原因——傷疤從手腕一直延伸到前臂上端,像地圖上的公路一樣十字交叉。”“當時的主治醫生在治療青少年患者方面擁有非常豐富的經驗。他很同情小姑娘,耐心地與她交談,一步步引導她敞開心扉。我們詢問了她的睡眠質量,因為睡眠過多或者過少都是抑郁癥的征兆。但有一件事情我們并沒有問——她的夢境。當時,我們并不認為夢境與她的自殘行為有關。”“后來我們意識到,沒有詢問她夢境相關簡直是大錯特錯。在美國,每年有超過4.4萬人自殺身亡,自殺已成為15歲至34歲人群的第二大殺手。統計數據顯示,有多達23%的青少年有過自殘行為。臨床醫生將其稱之為‘非自殺性自我傷害’。過去幾個月,已經有多項研究將噩夢與更高的自殺率聯系在一起。”
據悉,在美國,每年有超過4.4萬人自殺身亡,自殺已成為15歲至34歲人群的第二大殺手。統計數據顯示,有多達23%的青少年有過自殘行為。過去幾個月,多項研究將噩夢與更高的自殺傾向聯系在一起。8月2日,《紐約雜志》發表加拿大住院醫生和流行病學家阿米塔·卡萊查德蘭的一篇文章,講述噩夢與自殺傾向之間的關系。全文如下:噩夢已成第二大殺手“我接觸的第一位青少年自殘患者是一名16歲的醫科學生。她留著長長的褐色頭發,身穿長袖法蘭絨襯衫。她這身打扮讓我覺得有些怪異,我記得當時是7月中旬,但她卻穿著很厚的衣服,來到我的診所。等到她挽起袖子的時候,我才知道她這么穿的原因——傷疤從手腕一直延伸到前臂上端,像地圖上的公路一樣十字交叉。”“當時的主治醫生在治療青少年患者方面擁有非常豐富的經驗。他很同情小姑娘,耐心地與她交談,一步步引導她敞開心扉。我們詢問了她的睡眠質量,因為睡眠過多或者過少都是抑郁癥的征兆。但有一件事情我們并沒有問——她的夢境。當時,我們并不認為夢境與她的自殘行為有關。”“后來我們意識到,沒有詢問她夢境相關簡直是大錯特錯。在美國,每年有超過4.4萬人自殺身亡,自殺已成為15歲至34歲人群的第二大殺手。統計數據顯示,有多達23%的青少年有過自殘行為。臨床醫生將其稱之為‘非自殺性自我傷害’。過去幾個月,已經有多項研究將噩夢與更高的自殺率聯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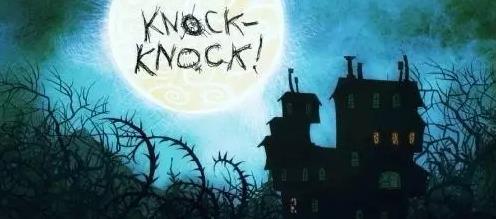 “在科學文獻中,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標準的噩夢定義。不過,絕大多數研究人員對噩夢的描述大同小異:高度煩躁焦慮的夢境,夢中的情境令人不安,經常讓人從沉睡中驚醒。最新版《診斷與統計手冊》(精神病診斷的圣經)收錄了一個夢魘癥條目,將噩夢定義為‘極端煩躁焦慮和無法忘懷的夢境,通常出現生存、安全或者身體完整性受到威脅的情境’。”可作為早期預警信號通常情況下,如果一個人經常做噩夢,我們會診斷他/她可能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這種患者可能經歷過戰爭,或者有過其它痛苦經歷。3月,《科學報告》雜志刊登了芬蘭土爾庫大學一支研究小組的論文。根據他們的研究,經常做噩夢也是一個自殺危險因素,即便是對非PTSD人群。此項研究由尼爾斯·桑德曼領導。桑德曼與“睡魔”同名,但他堅稱之所以研究噩夢并不是因為自己的名字。研究中,桑德曼等人對芬蘭國家風險研究項目1972年至2012年的數據進行了分析。該研究項目對參與者進行跟蹤調查,直至2014年或者他們去世。即使將參與者中的老兵排除在外,他們仍然發現頻繁做噩夢的人與自殺者之間的重疊具有重要的統計學意義。調查采用了這樣一個問題——你在過去30天是否做過噩夢?如果答案是“經常”,便被列為“頻繁噩夢的人”。桑德曼表示:“我們發現噩夢實際上是自殺的一個獨立風險因素,可以作為一個早期預警信號。醫生應該仔細詢問患者的夢境。”根據《綜合精神病學》雜志8月公布的一項研究,頻繁做噩夢也可能預示著自殘傾向。此項研究由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切爾西·伊尼斯和同事進行。通過分析兩個不同樣本——一組為存在心理問題的患者,一組為大學生,伊尼斯等人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聯系。即使抑郁癥癥狀得到控制,結果仍舊如此。伊尼斯表示:“研究顯示睡眠問題本身可能并不會導致自殘行為,但噩夢卻與更嚴重的情緒調節異常有關,進而導致更高的自殘風險。”她的發現與最近在中國山東進行的一項研究不謀而合,共有1000多名學生參與了該研究,研究發現經常做噩夢可導致自殘風險加倍。
“在科學文獻中,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標準的噩夢定義。不過,絕大多數研究人員對噩夢的描述大同小異:高度煩躁焦慮的夢境,夢中的情境令人不安,經常讓人從沉睡中驚醒。最新版《診斷與統計手冊》(精神病診斷的圣經)收錄了一個夢魘癥條目,將噩夢定義為‘極端煩躁焦慮和無法忘懷的夢境,通常出現生存、安全或者身體完整性受到威脅的情境’。”可作為早期預警信號通常情況下,如果一個人經常做噩夢,我們會診斷他/她可能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這種患者可能經歷過戰爭,或者有過其它痛苦經歷。3月,《科學報告》雜志刊登了芬蘭土爾庫大學一支研究小組的論文。根據他們的研究,經常做噩夢也是一個自殺危險因素,即便是對非PTSD人群。此項研究由尼爾斯·桑德曼領導。桑德曼與“睡魔”同名,但他堅稱之所以研究噩夢并不是因為自己的名字。研究中,桑德曼等人對芬蘭國家風險研究項目1972年至2012年的數據進行了分析。該研究項目對參與者進行跟蹤調查,直至2014年或者他們去世。即使將參與者中的老兵排除在外,他們仍然發現頻繁做噩夢的人與自殺者之間的重疊具有重要的統計學意義。調查采用了這樣一個問題——你在過去30天是否做過噩夢?如果答案是“經常”,便被列為“頻繁噩夢的人”。桑德曼表示:“我們發現噩夢實際上是自殺的一個獨立風險因素,可以作為一個早期預警信號。醫生應該仔細詢問患者的夢境。”根據《綜合精神病學》雜志8月公布的一項研究,頻繁做噩夢也可能預示著自殘傾向。此項研究由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切爾西·伊尼斯和同事進行。通過分析兩個不同樣本——一組為存在心理問題的患者,一組為大學生,伊尼斯等人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聯系。即使抑郁癥癥狀得到控制,結果仍舊如此。伊尼斯表示:“研究顯示睡眠問題本身可能并不會導致自殘行為,但噩夢卻與更嚴重的情緒調節異常有關,進而導致更高的自殘風險。”她的發現與最近在中國山東進行的一項研究不謀而合,共有1000多名學生參與了該研究,研究發現經常做噩夢可導致自殘風險加倍。
 勿將噩夢默認為“病態”不過,并非所有研究都發現了這種聯系。2013年,西弗吉尼亞州的一支研究小組指出,失眠預示著自殺風險,但頻繁做噩夢與自殺風險之間沒有聯系。之所以得出矛盾結果,部分原因在于我們并未完全了解噩夢的內容或者人在噩夢中的行為。一些研究人員指出,噩夢是對清醒時可能遭遇的各種威脅的一次“帶妝彩排”,或者在我們沉睡時中和消極情緒。然而,就像沒有標準的噩夢定義一樣,對噩夢的作用也沒有一個普遍接受的解釋。如何讓噩夢這個風險因素單獨隔絕使其不受其它因素影響(例如睡眠不佳、焦慮和抑郁)是一個不小挑戰。麻省總醫院的阿什亞·瓦哈扎德認為對噩夢和自殺的研究非常有趣。噩夢可能意味著情緒低落或者焦慮,而消極情緒與自殺風險有關。然而,絕不能簡單地將噩夢默認為一種“病態”。他希望未來的研究能夠在“如何定義噩夢”和“如何評估頻率”方面做出更多努力。瓦哈扎德說:“很多研究定義的噩夢都帶有一定的主觀性,未來的研究需要讓定義標準化,同時進一步明確噩夢與自殺意念之間的因果關系。”瓦哈扎德認為醫生不僅要關注患者的噩夢頻率,同時還要詢問患者是否存在睡眠障礙。“我們知道睡眠質量能夠影響情緒和我們的身體機能,反之亦然。二者之間雙向關聯。面對存在情緒問題的患者時,絕大多數醫生并沒有深入了解患者的睡眠質量。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情況正在逐漸改善,因為我們越發意識到睡眠質量對我們的情緒和總體健康狀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文章由企鵝科學和科普中國聯合推出轉載請注明來自“科普中國”
勿將噩夢默認為“病態”不過,并非所有研究都發現了這種聯系。2013年,西弗吉尼亞州的一支研究小組指出,失眠預示著自殺風險,但頻繁做噩夢與自殺風險之間沒有聯系。之所以得出矛盾結果,部分原因在于我們并未完全了解噩夢的內容或者人在噩夢中的行為。一些研究人員指出,噩夢是對清醒時可能遭遇的各種威脅的一次“帶妝彩排”,或者在我們沉睡時中和消極情緒。然而,就像沒有標準的噩夢定義一樣,對噩夢的作用也沒有一個普遍接受的解釋。如何讓噩夢這個風險因素單獨隔絕使其不受其它因素影響(例如睡眠不佳、焦慮和抑郁)是一個不小挑戰。麻省總醫院的阿什亞·瓦哈扎德認為對噩夢和自殺的研究非常有趣。噩夢可能意味著情緒低落或者焦慮,而消極情緒與自殺風險有關。然而,絕不能簡單地將噩夢默認為一種“病態”。他希望未來的研究能夠在“如何定義噩夢”和“如何評估頻率”方面做出更多努力。瓦哈扎德說:“很多研究定義的噩夢都帶有一定的主觀性,未來的研究需要讓定義標準化,同時進一步明確噩夢與自殺意念之間的因果關系。”瓦哈扎德認為醫生不僅要關注患者的噩夢頻率,同時還要詢問患者是否存在睡眠障礙。“我們知道睡眠質量能夠影響情緒和我們的身體機能,反之亦然。二者之間雙向關聯。面對存在情緒問題的患者時,絕大多數醫生并沒有深入了解患者的睡眠質量。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情況正在逐漸改善,因為我們越發意識到睡眠質量對我們的情緒和總體健康狀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文章由企鵝科學和科普中國聯合推出轉載請注明來自“科普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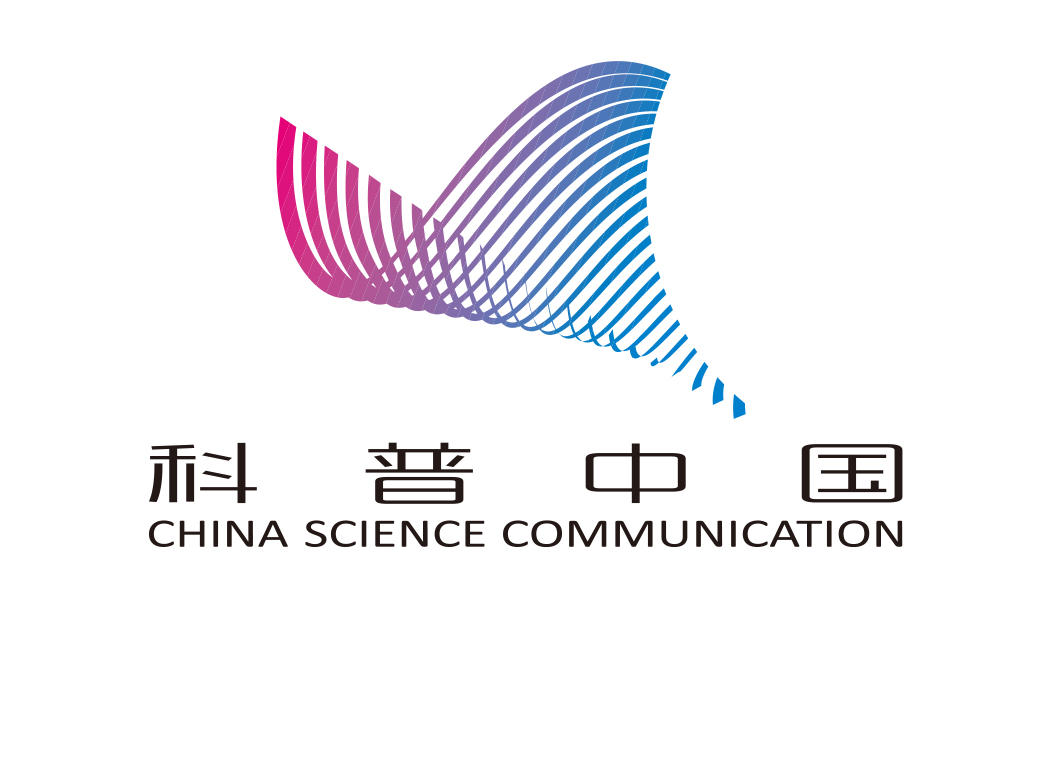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我們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微博
科普中國微博

 幫助
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