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錢維宏,北京大學物理學院
在一個寧靜的夜晚,一瓶中國白酒和一瓶法國紅酒被擺放在同一張餐桌上。它們靜靜地“對視”著,仿佛在進行一場關于釀造科學的深度對話。
對話1:原料、酒精度與文化印記
白酒:嗨,紅酒,很高興能和你一起探討我們背后的科學奧秘。雖然我們都屬于酒類,但從源頭看,差異就很明顯了。
紅酒:確實如此。我了解到,你的主要原料是高粱、小麥等糧食,對吧?而我則完全依賴葡萄。這是不是我們很多差異的起點?
白酒:沒錯。糧食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所以我的釀造需要先把淀粉轉化為糖,再發酵成酒精,過程更復雜些。最終我的酒精度數通常在40%vol至60%vol之間。
紅酒:這和我很不一樣。葡萄果肉中天然含有葡萄糖,不需要復雜的轉化步驟,通過酵母發酵就能直接生成酒精。所以我的酒精度數相對較低,一般在12%vol至15%vol左右,更適合搭配餐食慢慢飲用。
白酒:我們的歷史也都很悠久。我在中國已有數千年歷史,深深融入了傳統文化,無論是重要慶典還是日常宴請,都能看到我的身影,承載著團圓、熱情的文化內涵。
紅酒:我在歐洲的歷史也很悠久,是葡萄酒文化的重要符號,常與優雅、浪漫聯系在一起。在很多西方國家,晚餐搭配紅酒是一種生活方式,人們注重品味其中的果香和細膩口感。
白酒:聽說你們的陳釀對容器很講究,比如橡木桶?
紅酒:是的,橡木桶不僅能讓紅酒緩慢氧化,還會賦予它香草、煙熏等獨特風味,而且優質紅酒確實會隨時間沉淀得更出色。你們呢?
白酒:我們用陶壇陳釀。陶壇的透氣性有助于酒體的老熟,時間越長,酒體越醇厚,香氣也越協調。我們還有不同香型,比如醬香型、濃香型、清香型,每種香型都有其獨特的風味物質構成。
紅酒:看來我們雖然路徑不同,但都追求品質和風味的提升。其實,無論是哪種酒,核心都是給人們帶來愉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也能通過我們相互了解。
白酒:你知道嗎?用來釀我的高粱、小麥這些糧食沒法長期存放,人們把它們釀成白酒,就能長久保存啦。
紅酒:可不是嘛,葡萄也不耐存,釀成紅酒后,在合適的環境里就能放很久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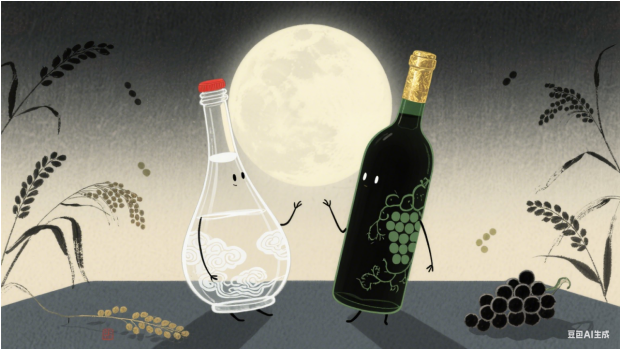
對話2:釀造工藝的科學邏輯
白酒:說到釀造,我一直覺得我們的工藝差異很有研究價值。你們的發酵主要是自然發酵嗎?
紅酒:準確來說,是依靠葡萄表皮天然附著的酵母菌群進行發酵。首先要挑選成熟的葡萄,壓榨得到葡萄汁,然后酵母會在其中生長繁殖,將葡萄糖轉化為酒精和二氧化碳。發酵過程中,我們還會通過攪拌或泵送,讓葡萄皮中的色素、單寧和香氣物質更好地融入酒液。這個過程中包含了外力對參與釀造粒子的動力學碰撞作用呢。
白酒:這和我們的“酒曲發酵”有很大不同。你們的酵母是天然存在的,而我們的發酵動力來自“酒曲”,也有外力的動力碰撞作用,如人工踩曲。
紅酒:“酒曲”是什么?能具體說說嗎?
白酒:酒曲是我們釀造的核心,它是一種富含微生物(如霉菌、酵母菌、細菌等)和它們分泌的酶類(如淀粉酶)的發酵劑。制作時以小麥、豌豆等為原料,經過特定工藝,如傳統的人工踩曲培養而成。在發酵中,這些微生物能將糧食中的淀粉轉化為可發酵糖,進而轉化為酒精,同時還會產生大量風味物質,比如酯類、醇類等。
紅酒:原來是這樣,相當于你們為發酵“定制”了微生物群落。那你們的發酵和后續處理還有什么特點?
白酒:我們的發酵容器多樣,有陶壇、泥窖和石窖、水泥池、不銹鋼罐等,發酵周期一般在一個月左右。發酵完成后,關鍵步驟是蒸餾——利用酒精與水的沸點差異(酒精沸點約78℃,水為100℃),通過加熱將發酵后的酒醅中的酒精及風味物質提取并濃縮,這也是我們酒精度較高的原因。
紅酒:蒸餾這個步驟我們是沒有的,因為我們希望保留葡萄發酵產生的原始風味。發酵結束后,我們會壓榨分離酒液,然后進入陳釀階段。
白酒:陳釀對我們來說也至關重要。蒸餾后的原酒要在陶壇中存放數年,期間酒液中的分子會發生氧化、酯化等反應,雜質逐漸揮發,口感才會變得柔和醇厚。有些產區還會利用山洞、地窖等恒溫恒濕的環境陳釀,更有利于酒體穩定。
紅酒:我們的陳釀也講究環境控制。橡木桶陳釀能讓酒液與微量氧氣接觸,單寧逐漸軟化,同時橡木中的風味成分會融入酒中,增加復雜性。不過,陳釀時間也要適度,并非越久越好。
白酒:看來發酵和陳釀是我們共同的關鍵環節,只是具體方式因原料和需求不同而有所差異。這些工藝細節,正是我們風味獨特性的來源。
對話3:產區差異的科學密碼
白酒:除了工藝,我們的產區差異也很有意思。我主要產自青藏高原東側的亞洲副熱帶季風區域,你知道這是為什么嗎?
紅酒:我猜和氣候有關吧?我們紅酒的核心產區也都有特定的氣候條件,比如半干旱或海洋性氣候區,像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就很適合葡萄生長。
白酒:沒錯,氣候是關鍵。青藏高原東側的季風區氣候濕潤,四季分明,年降水量和溫度都很適合微生物的多樣性和活性——而微生物對我們白酒的發酵太重要了。中國的白酒主產區,比如赤水河谷、長江-淮河-黃河名酒帶等,都受益于這種季風氣候。如果沒有青藏高原的地形影響,這里可能會是干旱帶,就很難形成適合釀造的微環境了。
紅酒:這和我們的產區邏輯有相似之處。葡萄生長需要充足的光照和適宜的溫差,半干旱地區能減少病蟲害,晝夜溫差大則有利于葡萄積累糖分和風味物質。比如智利的中央山谷、阿根廷的門多薩,都是這樣的理想產區。有趣的是,在中國北方的季風邊緣活動帶的半干旱地區,也很適合葡萄種植和紅酒釀造。
白酒:土壤也很關鍵。比如貴州茅臺鎮和四川茅溪鎮,位于赤水河谷,那里的土壤富含特定礦物質,能為微生物提供營養,同時河谷的“臂彎”地形形成了局部小氣候,土壤、濕度和溫度都非常適合醬香型白酒的釀造。
紅酒:我們也很看重土壤。智利中央山谷的土壤多為火山灰,排水性好,能促進葡萄根系深扎;阿根廷門多薩的土壤是沖積土,富含礦物質,加上高海拔帶來的強紫外線,能讓葡萄的糖分和色素積累更充分,釀出的紅酒單寧豐富、色澤濃郁。
白酒:這么看來,無論是白酒還是紅酒,產區的氣候(溫度、降水、光照)、土壤成分、地形地貌,都會通過影響原料品質或微生物活性,最終決定酒的風味和品質。這大概就是“一方水土養一方酒”的科學道理吧。
紅酒:完全同意。這些自然條件與人類工藝的結合,才造就了我們各自的獨特魅力。
對話4:釀造周期的時間密碼
白酒:聊了原料、工藝和產區,我還挺好奇咱們的釀造周期有多大差異。畢竟從原料到成品,這中間的時間跨度里藏著不少科學門道。
紅酒:確實值得好好聊聊。我們紅酒的周期相對“緊湊”,從葡萄采摘到成品上市,通常在1年到2年之間。你知道嗎?這和葡萄的生長周期密切相關——葡萄從開花到成熟需要整個生長季(大約6-8個月),而釀造本身的時間其實更短。
白酒:具體來說呢?比如發酵和陳釀各占多少時間?
紅酒:發酵階段很快,浸漬發酵一般只需要7-14天,酵母就能把葡萄汁里的糖分轉化得差不多。之后壓榨、澄清,進入陳釀階段。如果是即飲型紅酒,可能在橡木桶或不銹鋼罐里陳放3-6個月就可以裝瓶了;要是需要陳年的優質紅酒,橡木桶陳釀可能延長到1-2年,裝瓶后還會再瓶儲一段時間,但整體不會太久,畢竟葡萄的新鮮風味經不起太長時間的“消耗”。
白酒:這和我們比起來可真是“速戰速決”了。我們的釀造周期要長得多,尤其是傳統工藝的白酒,從制曲開始到成品出廠,往往需要幾年時間。醬香型白酒的釀造過程需要一年,為一個循環周期。
紅酒:這么久?能具體說說每個階段的時間嗎?我知道你們的“酒曲”很關鍵,制曲就要花不少時間吧?
白酒:沒錯,制曲本身就是個“慢功夫”。以濃香型白酒為例,制曲通常在夏季,小麥經過粉碎、加水、踩制成型后,要在曲房里培養40-60天,期間還要翻曲多次調節溫度和濕度,讓微生物充分繁殖。這還不算完,制成的曲還要存放3-6個月才能使用,目的是讓曲中的微生物代謝更穩定,減少雜味。
紅酒:單是制曲就快趕上我們整個釀造周期了。那后續的發酵和蒸餾呢?
白酒:對了,就拿制曲來說,不同香型差別可大了——我這醬香型用的大曲,制曲溫度得高達60℃以上,有的甚至能到65-70℃;濃香型呢,中高溫曲居多,一般在50-60℃;清香型就不一樣了,多是中低溫曲,溫度大概在40-50℃,這溫度差異還真影響著咱們的風味呢。醬香型白酒多出生在赤水河谷是因為那里的河谷的自然溫度就很高。
紅酒:沒想到你們白酒制曲充分利用了自然小氣候,還有這么多講究,溫度不同,釀出來的味道大不一樣。
白酒:發酵階段,糧食經過蒸煮、加曲后入池發酵,濃香型白酒的發酵周期一般是60-90天,醬香型則要更長,有的甚至達到180天。而且我們很多工藝是“續糟發酵”,就是每次發酵后留下部分酒糟,和新糧、新曲混合再發酵,這樣能延續微生物群落,也讓風味更厚重。發酵完成后蒸餾取酒,但這還不是成品——新酒的刺激性物質多,必須經過陳釀。
紅酒:陳釀要多久?是不是越久越好?
白酒:陳釀時間因香型而異。清香型白酒可能陳釀1-2年,濃香型需要3-5年,醬香型往往要5年以上。科學上講,陳釀是為了讓酒里的醛類、硫化物等低沸點雜質揮發,同時促進醇、酸、酯之間的酯化反應,讓酒體更柔和、香氣更協調。但也不是無限延長,達到最佳平衡后繼續存放,風味提升就不明顯了。算下來,一瓶優質白酒從制曲到出廠,少則3年,多則十幾年,這還沒算上原料種植的時間呢。
紅酒:看來我們的周期差異,本質是原料特性和工藝目標決定的。葡萄的新鮮風味需要及時保留,而你們則通過長時間的微生物轉化和陳釀,讓糧食的風味潛力充分釋放。
白酒:確實如此。不過無論是“快節奏”還是“慢功夫”,核心都是在時間維度上調控物質轉化,最終呈現出最佳風味。這大概就是釀造的時間美學吧。
結束語
白酒:聊了這么多,其實我一直很好奇,用你的釀造邏輯呈現的風味是什么樣的——那些葡萄的果香、單寧的澀感,一定和我們糧食發酵的醇厚很不一樣吧?
紅酒:我也正想嘗嘗你們經過蒸餾和陶壇陳釀的獨特風味呢。聽說醬香里的酯類物質有上百種,濃香型的窖香帶著歲月的厚重,這些都是葡萄發酵難以復制的層次。
白酒:不如我們換個方式“對話”?用各自的酒體做一杯跨界調和——比如用我的陳釀基酒搭配你的單寧,說不定能碰撞出既保留糧食底蘊,又帶著果香清新的新味道,開辟一條勾兌的新河。
紅酒:這個主意很棒!就像不同釀造智慧的交融,既能讓人們嘗到我們本來的特色,也能發現彼此的共通之處。或許這樣的嘗試,能讓更多人理解:好酒沒有高低,只是不同自然與工藝的誠實表達。也許,跨界調和酒的酒精度數和風味能夠適應更多的人群。
白酒:干杯!為了這場跨越地域的釀造對話,也為了更多人能讀懂我們背后的科學與故事。
紅酒:干杯!期待未來能在更多餐桌相遇,用風味續寫這場關于自然與時間的對話。
從原料特性到工藝邏輯,從產區風土到時間沉淀,白酒與紅酒的對話,實則是人類利用外力作用于微生物轉化自然饋贈的兩種智慧路徑。它們因地域文化而生差異——一個以糧食為基,借酒曲之力完成淀粉到酒精的復雜蛻變,在漫長陳釀中凝練醇厚;一個以葡萄為本,憑天然酵母實現糖分到酒香的直接轉化,于精準周期里鎖住新鮮。但終究又因釀造的共通規律而相通:都依賴微生物的代謝魔力,都受限于產區的風土密碼,都需要時間的耐心雕琢。這場跨越文化的對話,不僅讓我們看清了“酒”的科學本質,更讓我們讀懂了不同文明對“轉化”與“平衡”的獨特詮釋——而這,正是釀造藝術最動人的魅力。
來源: 錢維宏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微博
科普中國微博

 幫助
幫助
 錢維宏
錢維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