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生命比作一本書,那么基因就是其中的文字。人類花費了幾個世紀去理解這些文字的含義,而生物信息學(bioinformatics)正是解開這本生命之書奧秘的關鍵工具。它像是一座橋梁,連接著生物學和計算機科學,使科學家能夠解析海量的生物數據,從DNA序列到蛋白質結構,再到整個生態系統的動態變化。對于我們公眾來說,“生物信息學”這個詞,或許聽起來復雜而遙遠;但事實上,它的應用已經滲透到醫學、農業、環境科學等多個領域,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十世紀中葉,分子生物學的快速發展催生了對數據分析的需求。1953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英國劍橋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為生物信息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不過,真正推動這一學科發展的,還得數1990年代啟動的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了。這一宏大的科研工程,集合了全球數百位科學家,最終在2003年完成了人類基因組的完整測序。面對海量的基因數據,當時,傳統的實驗手段已捉襟見肘、難以應對;于是,科學家們開始依賴計算機算法和數據庫來存儲、分析和解讀這些信息,生物信息學由此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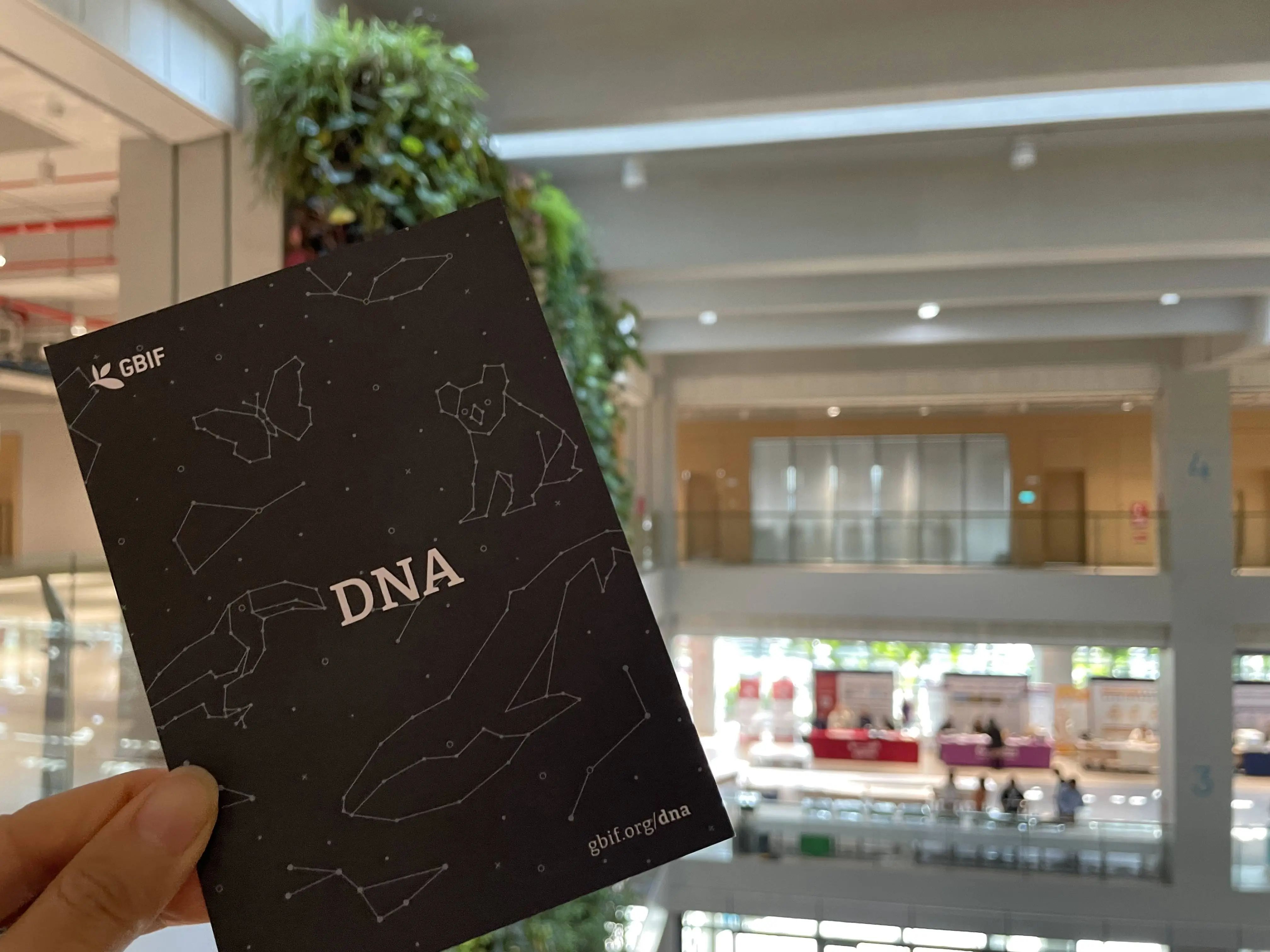
全球生物多樣性信息平臺(GBIF)與其他基因組數據庫、物種分布數據庫等進行整合,構建更加龐大的生物信息網絡。這使得研究人員可以更方便地獲取和分析多維度生物數據,深入挖掘生物多樣性背后的規律。上圖是一份GBIF的DNA介紹材料。?Linda Wong | 綠會融媒·“海洋與濕地”(OceanWetlands)
生物信息學的核心任務之一是序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我們知道,DNA和蛋白質的序列中蘊含著進化的密碼,科學家可以通過比對不同物種的基因組,追溯生命的演化歷史。例如,在1995年,美國科學家克雷格·文特爾(Craig Venter)領導的團隊成功測序了首個自由生活細菌——流感嗜血桿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的基因組。這一突破,不僅展示了基因組測序的可行性,也為生物信息學的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
今天,科學家可以使用BLAST(Basic Local Alignment Search Tool)等工具,在全球的基因數據庫中尋找相似的序列,以推測基因的功能。舉例來說,當新冠病毒在2019年底首次被發現時,科學家們迅速測序了其基因組,并利用生物信息學工具比對此前已知的冠狀病毒序列,從而確定了病毒的進化來源,并迅速開發檢測方法和疫苗。
蛋白質結構預測是生物信息學的另一個重要應用。蛋白質的功能取決于其三維結構,而解析這種結構傳統上需要昂貴且耗時的實驗方法,如X射線晶體學(X-ray crystallography)或冷凍電鏡(cryo-electron microscopy)。但近年來,人工智能在生物信息學中的應用取得了突破性進展。2020年,英國的DeepMind團隊開發的AlphaFold2算法成功預測了大量蛋白質的三維結構,其精度已接近實驗方法。這一成就,極大地加速了藥物研發和生物醫學研究的進程。
【法醫學中的DNA分析】
生物信息學在法醫學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幫助破案。例如,2018年美國警方利用開放式基因組數據庫GEDmatch,結合生物信息學方法成功破獲了**“金州殺手”**(Golden State Killer)案件。研究人員通過比對犯罪現場DNA與公開家譜數據庫中的DNA,確定了嫌疑人的遠親,并利用生物信息學工具構建家譜關系,最終鎖定了罪犯Joseph James DeAngelo。“金州殺手”案件的成功破獲, 展示了法醫基因組學在刑事偵查中的巨大潛力,并推動了這項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應用。
【古DNA研究揭示尼安德特人與現代人基因交流】
生物信息學在古人類學研究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揭示人類進化史方面。2010年,Svante P??bo 及其團隊利用先進的測序技術和生物信息學方法,成功完成了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基因組的測序。通過對尼安德特人基因組的組裝和分析,研究人員發現現代歐亞人群的基因組中約有 1-2% 的 DNA 來自尼安德特人。這一發現為我們理解尼安德特人與早期智人(Homo sapiens)在遷徙過程中的基因交流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進一步的研究表明,某些尼安德特人基因可能對現代人群的免疫系統和多種疾病的易感性產生影響。如有研究顯示,新冠病毒重癥患者中攜帶某些來自尼安德特人的特定基因變異的比例較高,但其具體作用機制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尼安德特人基因對現代人類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新冠病毒感染只是其中一個可能的例子。
尼安德特人基因組的測序和分析,是生物信息學在古人類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不僅幫助我們了解了尼安德特人的遺傳信息,還揭示了現代人類與尼安德特人之間存在復雜的基因交流歷史。隨著生物信息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在未來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尼安德特人基因的功能及其對現代人類的影響。
生物信息學還幫助科學家從古老的DNA樣本中提取信息,揭示人類進化史。2010年,Svante P??bo及其團隊成功完成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組的測序,并發現現代歐亞人基因組中約有1-2%的尼安德特人DNA。這一發現表明,尼安德特人與早期智人在遷徙過程中發生了基因交流。進一步的研究發現,某些尼安德特人基因可能影響現代人群的免疫系統和某些疾病的易感性,例如新冠病毒重癥患者中有較高比例攜帶來自尼安德特人的特定基因變異。
生物信息學的影響,還遠遠不止于醫學領域。
在農業領域,科學家利用基因組數據來培育更高產、更抗病的作物。例如,水稻(Oryza sativa)的基因組測序,來幫助研究人員識別出控制抗旱性和產量的關鍵基因,從而改良水稻品種,提高糧食安全。在生態保護方面,科學家利用DNA條形碼(DNA barcoding)技術,通過分析環境中的微量DNA片段來監測生物多樣性。又比如說,在亞馬遜熱帶雨林中,研究人員通過水樣中的DNA分析,發現了許多此前未知的魚類物種,為生態保護提供了寶貴的數據。

潛水員在水下懸崖接近一只正在休息的綠海龜。?攝影:王敏幹(John MK Wong) | 綠會融媒·“海洋與濕地”(圖文無關)
生物信息學的發展,離不開強大的計算能力和數據存儲。隨著高通量測序技術(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的進步,基因數據的增長速度,遠超了摩爾定律。今天,全球最大的基因數據庫GenBank存儲的數據量已超過數十億個序列。如何高效地存儲、管理和分析這些數據,成為計算機科學家和生物學家共同面臨的挑戰。云計算和分布式計算正在成為生物信息學研究的重要工具,使得科學家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共享和處理數據。
【遠古基因組揭示消失的生物多樣性】
2021年,一項研究分析了從格陵蘭島采集的200萬年前的環境DNA樣本,發現該地區曾經存在猛犸象、馴鹿和樺樹(Betula spp.),這表明當時格陵蘭島可能存在這些物種,并暗示了該地區可能存在一定的生態系統。
【珊瑚基因組研究助力應對氣候變化】
全球變暖導致珊瑚白化現象加劇,許多珊瑚物種瀕臨滅絕。2021年,研究人員通過生物信息學分析,發現了某些珊瑚物種(如柄指珊瑚 Acropora digitifera)中的HSP70基因家族在抗熱應激中起關鍵作用。利用這些數據,科學家們正在嘗試通過基因編輯或人工選擇培育更耐熱的珊瑚,以增強珊瑚礁生態系統的適應能力。此外,生物信息學在分析珊瑚-共生藻(Symbiodinium spp.)的基因組時發現,不同種類的共生藻對溫度變化的耐受性不同,這一研究為珊瑚礁恢復和人工繁育提供了新策略。
【通過基因組研究拯救瀕危物種】
生物信息學技術已被用于瀕危物種的基因組保護和種群管理。比如說,加州禿鷹(Gymnogyps californianus)在20世紀80年代幾乎滅絕,僅剩27只個體。科學家通過基因組分析發現,該物種經歷了長時間的遺傳瓶頸效應(genetic bottleneck),導致其遺傳多樣性極低。基于這些數據,保護學家制定了科學的人工繁殖和遺傳管理計劃,成功使其種群數量增長至500只以上,并實現了重引入野外。
【通過eDNA監測瀕危物種】
傳統的生物多樣性調查方法往往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而環境DNA(eDNA)技術結合生物信息學分析,為物種監測提供了高效的手段。如,2022年,科學家在馬來西亞的河流中利用eDNA檢測到了極度瀕危的馬來貘(Tapirus indicus),這一發現為該物種的保護提供了關鍵數據。
在海洋生態研究中,研究人員利用eDNA技術在大堡礁中檢測到了40多種珊瑚的遺傳信息,即使這些珊瑚群落已在水下崩解,它們的DNA仍然能夠被捕獲并分析,為珊瑚礁修復提供了科學依據。
對于初學者而言,進入生物信息學的最佳方式是學習編程,尤其是Python和R語言。這兩種編程語言在數據分析和可視化方面極具優勢。有許多免費的在線課程和資源,如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NCBI)提供的教程,可以幫助學生掌握生物數據分析的基本技能。此外,參與實際項目也是學習的好方法。例如,許多科學家會在GitHub等平臺上公開自己的生物信息學工具和數據集,初學者可以通過參與這些開源項目來積累經驗。
生物信息學不僅僅是一門學科,更是一場正在改變世界的科學革命。它讓科學家得以探索生命的最基本組成部分,并將這些知識應用于醫學、農業和生態保護等領域。從測序第一個細菌基因組,到預測蛋白質結構,再到追蹤全球病毒變異,生物信息學始終站在生命科學的前沿。對于未來的生物信息學家而言,掌握編程、統計和生物學知識,將為他們打開探索生命奧秘的大門,也讓他們有機會在科學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跡。
【思考題】學而時習之
Q1、生命科學研究正朝著多尺度、多組學的方向發展,產生了海量的基因組、轉錄組、蛋白質組、代謝組等數據。如何有效地整合這些不同來源、不同尺度的生物學數據,打破“數據孤島”的現狀?以及,未來的生物信息學研究是否能發展出新的理論和方法,實現跨組學、跨尺度的知識發現與重構,從而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生命現象?你怎么看呢?
Q2、最近春節期間Deep Seek火了一把。隨著人工智能的崛起,生物信息學是否會淪為**“工具”學科**?如何與AI深度融合,實現學科的創新發展?
Q3、生物信息學的發展,是否會加劇**生物學研究的“馬太效應”?我們知道,生物信息學研究需要大量的計算資源、專業知識和數據積累。隨著生物信息學的日益重要,是否只有少數擁有強大資源、技術實力的機構,才能在該領域取得突破?這是否會加劇生物學研究的“馬太效應”——使得強者更強,弱者更弱?**你覺得,如何應對這一潛在的挑戰,促進生物信息學研究的公平發展?
Q4,筆者近幾年參加了國際基因組學大會(ICG),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對于基因組學的論文刷刷不斷的發布,一些傳統生物學家表示不屑。**我們知道,基因組學研究通常需要大量的計算資源和生物信息學分析。那么這里有一個有趣的問題:這種“大數據”的研究模式,是否會擠壓傳統生物學研究的空間?那些沒有條件開展基因組學研究的科學家,是否會因此失去科研競爭力?“小科學”也有其獨特的價值,例如對特定物種或生態系統的長期觀察和研究。從學術論文發表、評職稱等趨勢上看,是否應該更加重視“小科學”在生物學研究中的作用,避免“唯基因組論”的傾向?
Q5, 在精準醫學、合成生物學等新興領域的推動下,生物信息學如何應對**“個性化”與“標準化”**的矛盾,實現規模化應用與倫理考量的平衡?
(注:本文僅代表資訊。不代表平臺觀點。歡迎留言、討論。)
文 | 王芊佳
編輯 | Linda
排版 | 綠葉參考資料略
來源: 海洋與濕地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微博
科普中國微博

 幫助
幫助
 中國綠發會
中國綠發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