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科幻大作《降臨》,可能是第一個(gè)認(rèn)真探討外星人語言學(xué)的電影,在外星飛船突降地球之際,語言學(xué)家露易絲受遣去轉(zhuǎn)譯外星人的語言,不同于地球人按線性時(shí)間語序梳理文字,外星生命使用的是一種非線性的表意文字,這種文字看起來就像個(gè)圓環(huán)(見圖1),文字間沒有間隙,筆筆勾連交織,但抽掉任何一筆,整個(gè)句子的結(jié)構(gòu)就將全然不同。這說明早在下筆之前,書寫者就已經(jīng)知道整個(gè)句子的全部布局。露易絲通過頻繁和外星人接觸理解了它們的文字,然后劇變發(fā)生了:她能看到未來的事情碎片般地在眼前閃回,過去、現(xiàn)在、未來成為了一個(gè)整體。電影的邏輯很清晰:語言的形式?jīng)Q定了使用者的思維方式,外星語言的圓環(huán)結(jié)構(gòu)無關(guān)先后,所以使用者沒有時(shí)間觀念,他們?nèi)P、并舉、整體地理解并把握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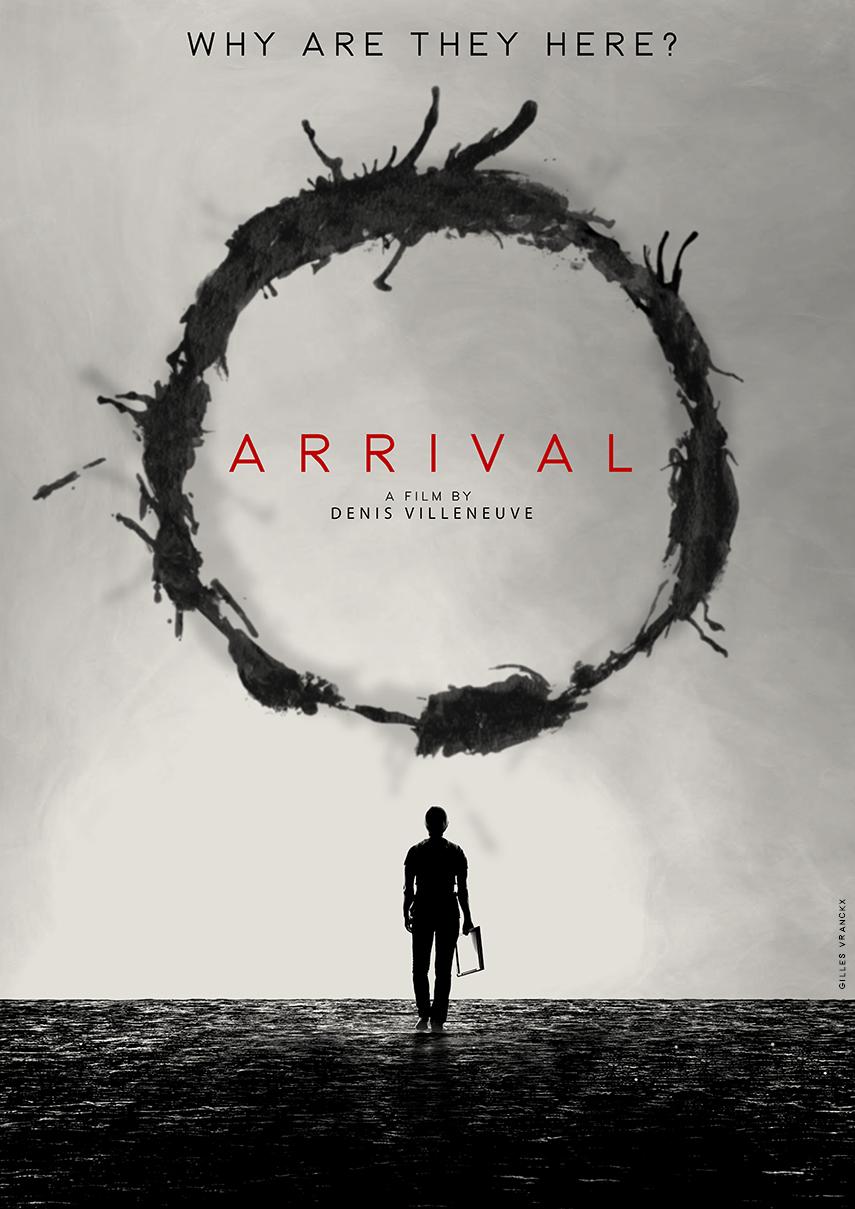
圖1 電影《降臨》(英文名:ARRIVAL)海報(bào)圖源:google picture, Crective Commons License
當(dāng)然這后面就要牽扯到老生常談的時(shí)間悖論問題了:露易絲要是改變了現(xiàn)在,那未來又怎么會(huì)原封不動(dòng),電影是這樣解釋的:學(xué)會(huì)了外星語,露易絲已經(jīng)不是人類的思維方式了,她的目的就是要使已知的事實(shí)逐步實(shí)現(xiàn)。總之別問為什么不改變現(xiàn)在,反正她就這么想了。這就形成了幾個(gè)很有沖擊力的問題:我們的語言是否限制了我們的潛能?它真的能夠塑造文明的思維方式嗎?它又是否反映了真實(shí)的世界?
完美語言
語言,是人類用來表達(dá)內(nèi)心思想與感情的媒介,這點(diǎn)是沾了老祖宗的光:人類共同的祖先是非洲南方古猿,抽象語言玩得轉(zhuǎn),據(jù)語言學(xué)家證明,越抽象的語言越能協(xié)調(diào)更大范圍的群體行為,憑借著這種非對(duì)稱優(yōu)勢(shì),祖先們樹立了霸主地位,走出了非洲,把基因傳播到全世界。有些“怒其不爭(zhēng)”的是,進(jìn)化了200萬年,我們的語言依舊非常原始低效,本質(zhì)還是用聲帶的振動(dòng)產(chǎn)生聲音,難以兼顧語速和信息密集度,語言學(xué)研究表明,受限于說者的表達(dá)能力與聽者的接受能力,現(xiàn)存語言在單位時(shí)間內(nèi)傳遞的信息量都差不多,每秒39比特,大約為莫爾斯碼發(fā)送速度的兩倍。用如此遲鈍的聲音來表達(dá)心中的細(xì)膩思想,簡(jiǎn)直就像用拖把沾墨來畫工筆畫一樣費(fèi)勁。
能不能構(gòu)造一種高效的完美語言,使其攜帶的信息量最大呢?我們把描述一個(gè)系統(tǒng)需要的最小存儲(chǔ)空間長(zhǎng)度,定義為信息熵,信息熵最大的語言必然最靠近信息壓縮下界,即任何文本壓縮算法到達(dá)這個(gè)界限再也無法壓縮,無法再被壓縮優(yōu)化的語言就是完美語言。主流語言中最接近文本壓縮界限的是中文,信息熵是英、法、俄語的兩倍還多,聯(lián)合國(guó)同一文件的六種官方文本中,最薄的總是中文,這樣看來,中文算是主流語言中的完美語言了。可實(shí)際交流中,中文并不比英語高效,原因是:如果一個(gè)詞的信息熵太高了,人們就傾向于減慢發(fā)音速度,減小說者和聽者的語言加工負(fù)擔(dān),所以中文是字正腔圓擲地有聲,而英文總是語速連珠帶炮如飛一般(經(jīng)常看美劇的讀者會(huì)有所體會(huì)),語速和信息熵的不可兼得,使這兩種語言都沒法超過每秒39比特的信息傳遞速率。這樣看下來,與其說日常語言限制了我們的潛能,倒不如說我們的潛能限制了日常語言,要構(gòu)造完美語言,得先提高人腦對(duì)語言信息的加工能力了。
語言相對(duì)論
直觀來看,人進(jìn)行的所有思維都和語言有關(guān),文字本質(zhì)上也是語言,只不過是無聲的語言,特殊群體使用的手語則是肢體語言,我們用語言給萬事萬物指定名稱,使曾經(jīng)的不可名狀之物有了人間的姓名,語言之于社會(huì),猶如空氣之于人,人是無法離開空氣存活的,但他常常會(huì)忽略空氣的存在。
認(rèn)為語言決定思維的觀點(diǎn)被稱為語言相對(duì)論(又稱薩丕爾-沃爾夫假說),電影《降臨》就是擴(kuò)張版本的語言相對(duì)論,背后思想是:語言改變了我們認(rèn)知世界的方式,認(rèn)知結(jié)構(gòu)的改變,決定了思維方式的改變。換句話說,語言的區(qū)別即是世界觀的區(qū)別。現(xiàn)實(shí)有很多例子可以佐證這點(diǎn):歐洲一些語言有幾十種表示顏色的詞匯,使用者需要從小刻意去辨別這些顏色,來練習(xí)色彩的精確表達(dá);而非洲的個(gè)別語言中僅有黑白兩種顏色詞語,他們對(duì)大多數(shù)顏色只有模糊的概念,這就使得后者對(duì)顏色的感知能力比前者要差。除了色彩語,方位語的不同也能導(dǎo)致方向感的不同,某些原始部落的語言使用東南西北而不用前后左右,對(duì)我們來說,無論我們轉(zhuǎn)向哪里,我們的視線永遠(yuǎn)在我們腦袋的前面,但對(duì)這些原住民,換個(gè)方向,視線就從腦袋的南面變成北面了,絕對(duì)方位的使用使他們擁有超乎常人的導(dǎo)航能力,即便是在沒有星星的晚上,也能很好地辨認(rèn)地理方向。所有這些例子都表明:語言不僅是思維的工具,還會(huì)對(duì)思維過程產(chǎn)生極大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能在潛移默化間塑造我們的思維面貌。
日常語言中,人們往往喜歡用感情極致的流行語來交流,不需要分辨“有口皆碑”和“嘆為觀止”的區(qū)別,一個(gè)“yyds”就包攬一切。殊不知,什么情況下都是yyds,也就模糊了情感程度的分別,模糊了辨析對(duì)象之間的精細(xì)差別,無疑也會(huì)誘導(dǎo)思維變得籠統(tǒng)單一。我們用以表達(dá)世界的詞語越多,我們對(duì)世界的理解也就越趨于準(zhǔn)確,在這個(gè)意義上,拓展我們的詞匯量,也是以細(xì)化顆粒度的方式拓展我們思維的邊界。
悖謬不謬的日常語言
許多話語聽起來一套一套的,但說話者其實(shí)并不清楚自己談?wù)摰牡降资鞘裁础1热纭白杂伞币辉~,人們喜歡在各種場(chǎng)合使用它,但“自由”實(shí)際屬于最難解釋含義的詞一類,是物質(zhì)優(yōu)越、無憂無慮的生活更自由?還是嚴(yán)格約束自我、不受自身欲望驅(qū)使的生活更自由?對(duì)這些關(guān)于“自由”定義的基礎(chǔ)問題,使用者往往并不清楚。究其原因,掌握精確表達(dá)的能力需要經(jīng)年累月的刻意練習(xí),而多數(shù)人往往接觸不到需要精確表達(dá)的生活場(chǎng)合,日常語言就成了未經(jīng)審視的不規(guī)范用語。
日常語言還充斥著自相矛盾,像“公開的秘密”,“單獨(dú)在一起”,“小心翼翼又漫不經(jīng)心”等,兩個(gè)互相矛盾的詞可以放在一個(gè)句子里,這些句子無疑是有問題的,但憑借主觀感覺,人們總能游刃有余地處理它們,為什么“寧死不屈”和“負(fù)隅頑抗”呈現(xiàn)兩種截然相反的意思?為什么“堅(jiān)定”是褒獎(jiǎng),而同樣字面意思的“頑固”卻是貶損?人們根據(jù)自身經(jīng)驗(yàn)和立場(chǎng)的不同,主動(dòng)從詞語中吸收了迥異的情感色彩,使語言從字面意思中分離出更深的“意”,本應(yīng)被視為自相矛盾的句子就孕育出了語意空間。
語意空間富有張力的存在,使這類句子在詩歌中俯拾皆是,比如詩人多多的《在這樣一種天氣里來自天氣的任何意義都沒有》:“土地沒有幅員/鐵軌朝向沒有方向/被一場(chǎng)做完的夢(mèng)所拒絕/被裝進(jìn)一只鞋匣里/被一種無法控訴所控制”,這首詩中的幾乎每一句都在自反(包括題目),后面的詞語破壞了前面詞語的字面意思,但讀者從中卻能感受到一種彌漫著絕望和虛無的情緒。
這些指涉性和邏輯性錯(cuò)誤的句子,也向我們表明了一點(diǎn):人們已然習(xí)慣從有歧義的語言中提取信息。當(dāng)筆者祝愿讀者們?cè)缛諒闹绷⑿凶哌M(jìn)化到飛升太虛時(shí),這種祝愿并不是完全不切實(shí)際的廢話,因?yàn)樗谋磉_(dá)同樣在說明自身的不現(xiàn)實(shí)。
別輕視這些充滿悖論的詩歌語言,科學(xué)家的真理需要一種肅清任何悖論痕跡的語言,但詩人的真理卻要依靠悖論,悖論所顯示的,是一種“不可言說之物”,分析哲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維特根斯坦認(rèn)為:詩歌中的“不可言說之物”閃耀在人類的精神世界中,這些和科學(xué)一樣,都是人類為了趨近終極之問作出的嘗試。
我們所能表達(dá)的世界受限于我們的語言能力,而語言是有局限的,世界的意義并非可以用語言完全表達(dá),它同樣以一種不可言說的方式顯示自己,就像禪,不能說,一說就破,所以,別僅僅依賴語言,嘗試去體驗(yàn)、去感受吧,去在融會(huì)貫通中理解它所顯示的意義。
聽者也說出了話
人類語言是人類思維的產(chǎn)物,但它并不能將說者的思想完全傳遞給聽者,語言是由語音、單詞和語法結(jié)構(gòu)組成的,它有內(nèi)在的指涉性和邏輯性,除非這種邏輯是純粹完備的,否則我們不可能實(shí)現(xiàn)全部的語義傳達(dá)。說者的腦袋內(nèi)部需要把語義翻譯成符號(hào),這句話才能說出來,而話語從符號(hào)翻譯成語義,必須借助說話人的語境,這個(gè)語境既包括說話人所處的環(huán)境,也包括說話人自己(自身經(jīng)驗(yàn)、立場(chǎng)等),換言之,一句話的意思不是由說者決定的,而是由說者和聽者共同決定的,某種意思上,當(dāng)這句話從說者的口中說出去時(shí),他就已經(jīng)喪失了對(duì)這句話的解釋權(quán),語言的靈魂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同的語境文化中不斷流動(dòng)變化的,聽者語境的不同,決定了任何指望語言符號(hào)傳達(dá)全部語義的看法都是不切實(shí)際的。
能不能繞過聽者,構(gòu)建一種私人語言,來使語言傳達(dá)出全部的語義呢?討論這個(gè)問題時(shí)要考慮到,說者的年齡會(huì)長(zhǎng)大,他自身的語境也會(huì)發(fā)生變化,所以為了語義的完全,他同樣不能說給自己聽,而一個(gè)不面對(duì)任何對(duì)象的語言,毫無疑問是沒有實(shí)際意義的。語言的本質(zhì),就像哲學(xué)家休謨說的那樣,是一種公眾事物。
在普遍的公眾之中,“我”是什么呢?“我”不過是黑暗洞穴里微乎其微的存在,世界于“我”是被火光投射到洞壁上的陰影,陰影不是實(shí)物,篝火在“我”的眼里是涌動(dòng)的黃色,在全色盲眼里是只有明暗之分的灰色,在皮皮蝦眼里是怪誕的彩虹色,但它只是反射了565-625nm波長(zhǎng)范圍的光,作為客體的顏色是不存在的,那只是以人的視角感知到的現(xiàn)象世界。
身處現(xiàn)象世界,我們永遠(yuǎn)無法得知物質(zhì)世界在其它的洞穴中映照出的影像,真實(shí)的世界究竟怎樣,猶如一團(tuán)無定形的云霧,而唯一能夠使這團(tuán)云霧凝結(jié)的,不是眼中所見,而是口中所言。在《霧都孤兒》之前,倫敦并沒有霧;在“剪不斷,理還亂”之前,我們不知道離愁可以如線。盡管語言永遠(yuǎn)不能傳達(dá)個(gè)人全部的心靈體驗(yàn),但它能夠給每個(gè)人的洞穴賦予聯(lián)系,聽說者的話,聽者自己也會(huì)感同身受,仿佛這話是由他的口中說出的一樣,他確信,他的腦中一定發(fā)生了什么變化,那是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的突觸間由電信號(hào)架起的新聯(lián)系通道,憑借著這些聯(lián)系,聽者才能理解說者,我們才能在這個(gè)雜草叢生的世界里相知相愛。
參考文獻(xiàn)
[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08487
[2] https://news.sina.com.cn/o/2019-07-04/doc-ihytcerm1290658.shtml
[3] Aceves, Pedro, and James A. Evans. "Human languages with greater information density have higher communication speed but lower conversation breadth." Nature Human Behaviour 8.4 (2024): 644-656.
[4] Coupé, Christophe, et al. "Different languages, similar encoding efficiency: Comparable information rates across the human communicative niche." Science advances 5.9 (2019): eaaw2594.
[5] https://njucml.nju.edu.cn/5a/11/c22619a350737/page.htm
[6] Wittgenstein, Ludwig.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Translated by 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Routledge, 1961.
來源: 星空計(jì)劃
內(nèi)容資源由項(xiàng)目單位提供


 科普中國(guó)公眾號(hào)
科普中國(guó)公眾號(hào)
 科普中國(guó)微博
科普中國(guó)微博

 幫助
幫助
 科普中國(guó)創(chuàng)作培育計(jì)劃
科普中國(guó)創(chuàng)作培育計(jì)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