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抗抑郁藥物氟西汀(百優解)第一篇論文發表50周年,自其問世以來,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類抗抑郁藥(SSRIs)就成為治療抑郁癥的首選方案,但作用機制和有效性一直飽受爭議。2022年一篇綜述論文更是將對SSRIs的質疑推上風口浪尖。從血清素假說、臨床試驗結果以及學界對抑郁癥的不同看法,我們可以看出SSRIs類藥物在抑郁癥治療中的復雜性和挑戰。
撰文 | 汪汪
2024 年是關于氟西汀(Fluoxetine)的第一篇論文發表的50 周年[1],提起氟西汀,它的另一個名字可能更廣為人知——百優解(Prozac;該藥中文名經常被誤寫作“百憂解”)。作為第一個上市的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類抗抑郁藥(SSRIs,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氟西汀在 1988 年上市后廣受歡迎,銷售額連年增長。在其之后,多個SSRIs類藥物上市,氟西汀、帕羅西汀、舍曲林、氟伏沙明、西酞普蘭更是被稱為抗抑郁藥物的“五朵金花”,牢牢占據著抗抑郁藥物的市場,SSRIs也成為大多數醫生給出治療建議時的首選方案。2022 年,英國共開出 4600 萬張 SSRIs 處方,其中 2100 萬張屬于 SSRIs 類藥物舍曲林,是當年處方量排名第十的藥物,而同年處方量最大的藥物阿托伐他汀的也僅為5700萬[2]。
銷量極大,醫生首選,患者能從中受益,這一切看起來,SSRIs的效果似乎毋庸置疑。但近年來,SSRIs的起效機制引發了很大的爭議,使得人們開始懷疑:這類藥物真的有用嗎?
血清素假說爭論再起
判斷藥物是否真的起效,我們往往要從藥物的作用機制和患者療效這兩方面來分析。SSRIs的全稱是血清素[5-羥色胺 (5-HT)]再攝取抑制劑。血清素是一類在大腦中廣泛分布的神經遞質。如果把我們的大腦想象成一簇一簇神經元的連接,那么血清素就是神經元間溝通的信使,介導神經信號的傳遞,對維持大腦的正常功能不可或缺。血清素能夠讓人類產生“愉快”體驗,它還參與了調節體溫、睡眠、性欲等多項生理功能[3]。關于抑郁癥的血清素假說就是基于這一點:若大腦中的血清素水平下降,可能會引發人類的抑郁癥狀。而SSRIs就是一類阻止血清素“回收”從而提高腦內血清素濃度來達到抗抑郁效果的藥物。
血清素假說的提出源于偶然。作為抗組胺過敏藥物發明的丙咪嗪無意中被發現可以讓人類產生愉悅的效果,從而成為第一種三環類抗抑郁藥物,三環類藥物雖然被證實具有抗抑郁效果,但也具有較為明顯的毒副作用。當時的科學家并不知道這些藥物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隨著研究逐漸增多,研究人員發現三環類藥物可以與多種神經遞質的受體結合,抑制突觸前膜對去甲腎上腺素(NA)、血清素和多巴胺(Dopamine)的再攝取,增加突觸間隙中這些神經遞質的濃度以延遲作用于相應受體的時間,從而發揮抗抑郁作用。
三環類藥物能結合多種受體,意味著它對這些神經遞質沒有選擇性,也意味著副作用的增加。為了將副作用降到最低,研究人員將目光集中到一種特定的蛋白質上:血清素轉運蛋白。這也推動了第一個SSRIs藥物——氟西汀的上市。(關于氟西汀的研發歷程,可參見《為了發明治抑郁癥的良藥,研究者沒少抑郁》)
但血清素的缺乏真的是導致抑郁癥的罪魁禍首嗎?后續的研究者并不這么認為,多項臨床研究都表明:血清素的抗抑郁效果被放大了。盡管這類藥物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患者的抑郁癥狀,但血清素失衡假說的前提“血清素的減少會引發抑郁癥”在多年來備受爭議。
2022 年,倫敦大學學院精神病學家Joanna Moncrieff及其合作伙伴在Molecular Psychiatry 雜志上發表了一篇綜述論文,通過對多個研究領域與血清素假說相關的論文進行分析整合和評估,最后得出結論:并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血清素水平降低會導致抑郁癥”,也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血清素水平和抑郁癥相關[4];而人為地降低健康人群大腦中的血清素水平也并沒有迅速導致抑郁癥的發生[5]。人們已經習慣了抑郁癥與血清素失衡有關的觀點,以至于這篇論文的結論引發了軒然大波,抗抑郁藥物領域來了一場小小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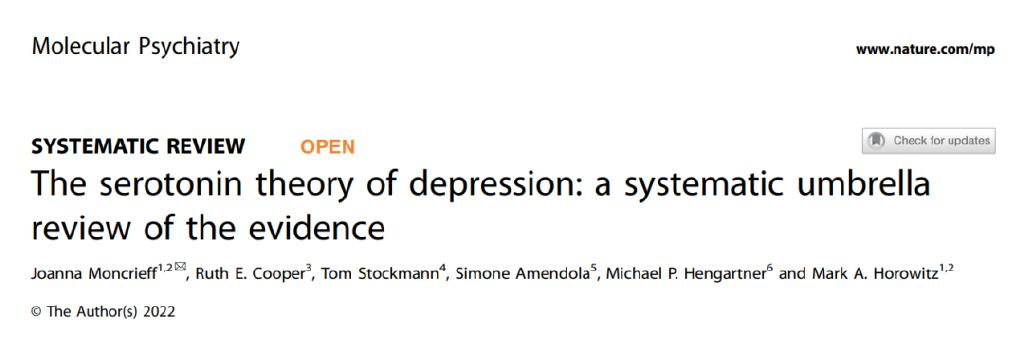
評價藥物效果更加直觀的方式是對患者的療效。SSRIs在這五十年里,占據了抗抑郁藥物的大部分市場,從這方面來看,它們的療效似乎毋庸置疑。但過往的多篇研究質疑了這一點。從統計學角度看,SSRIs 可能對抑郁癥狀有顯著效果,但對臨床研究的數據進行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在這些藥物的臨床試驗中,安慰劑也有很好的效果,以至于SSRIs的臨床意義也值得懷疑[6-7]。
此外,與安慰劑相比,SSRIs可能會增加某些不良事件的風險:數據表明,SSRIs的使用會導致癲癇和骨折的風險有所增加;在與某些藥物合用時,出血事件的風險也會增加。SSRIs對死亡率的影響似乎沒有顯著差異。但有研究表明,SSRIs的使用與自殺風險增加之間可能存在聯系。2007年,在禮來公司的另一款抗抑郁藥度洛西汀(Duloxetine,5-HT和NE再攝取抑制劑)臨床試驗期間,一名學生上吊自殺,這使得這款藥物引發了很大的爭議。同年,針對因涉嫌隱瞞抗抑郁藥相關臨床數據的訴訟,葛蘭素史克公司選擇公開臨床試驗結果,以便所有信息都能公開獲取。禮來公司迫于壓力,也決定發布臨床結果[8]。關于SSRIs療法與自殺風險增加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系,存在激烈的爭論。研究人員表示,在患者群體較為脆弱時,很難評估這種增加的風險是因為治療需要時間才能見效,還是因為SSRIs直接影響了情緒。
如此看來,近些年SSRIs 不斷遭受質疑,那為何依然如此暢銷,相關處方如雪花般紛飛開出是否存在濫用嫌疑?
學界對抑郁癥的看法存在沖突
作為三環類抗抑郁藥物之后的第二代抗抑郁藥物,盡管在SSRIs之后,還有更多新機制的藥物上市,但SSRIs依然是當前治療抑郁癥戰場上的主力軍,它的經久不衰當然是有原因的。一部分原因直觀可見:對于很多病人來說,SSRIs是有效的。雖然個體間存在差異,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在醫學上是相當正常的。來自芬蘭赫爾辛基大學(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的Eero Castrén對此評價:“盡管SSRIs的效果存在爭議,但這種藥物在臨床上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抗抑郁藥的療效確實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這種效果對一些人群和一些癥狀并不適用,但對很多病人來說,它們確實有效果,甚至是非常有效果。有很多治療高血壓的藥物,它們對很多人無效。但沒有人對此抱怨。” Castrén認為圍繞抑郁癥的污名化問題使得抗抑郁藥物更具有爭議性。
還有一些研究人員認為這是因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對抑郁癥的看法存在沖突:生物化學領域的研究人員希望了解抑郁癥期間我們的大腦中發生了什么,以及我們是否可以利用這些過程來幫助患者。與此同時,社會學領域的研究人員指出,藥物只能治療抑郁癥的癥狀,這可能掩蓋或分散人們對抑郁產生的社會背景的探尋。
引發爭議的論文作者Moncrieff認為人們把血清素和抑郁癥聯系在一起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應有的程度。她說道:“一直以來醫學界都有一種強烈的愿望,想要把抑郁癥看作是一種生理疾病,并相信我們有一種治療方法,用生物化學方法來可以治療患者的情緒低落。”
抑郁癥如果僅僅是一種生理疾病而且可以被治療,那這種情況對制藥公司和精神科醫生就會十分有利,因為大量的抗抑郁藥處方意味龐大的利潤。這種情況對政策制定者來說也是一件省心的事情,因為這避免了患者以其他方式應對“社會普遍的不滿”。要知道,抑郁癥的高發病率常常與糟糕的社會現實相關聯。因此,Moncrieff認為正是這些阻礙了我們更深入地去思考和探究SSRIs的工作原理。
這聽起來十分合理,如果你是政客,當抑郁癥在人群中高發時,你可以直接把問題轉給專家,轉給醫生和研究如何治療的科研人員,而不必去思考“為什么我們的社會中有這么多人不快樂?” ,更不必去想“這是否與社會的經濟狀況下行、與貧困和不平等的現狀有關?” Moncrieff最后說道:“我們正在將社會和經濟政策的后果轉移至醫學領域,而忽略了這些政策背后的現實——高失業率、住房和經濟無保障等等。”[2]
一切只是時間問題
2022年Moncrieff的綜述發表后,SSRIs的存在和使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很多人把這篇論文當成揮舞的旗幟,用以攻擊SSRIs和現有的精神病學。這種攻擊性的言論其實十分危險,雖然我們已經知道SSRIs并不完美,但至少在一些患者身上起作用了,而且對一部分患者來說,效果之好無異于靈丹妙藥。當公眾接受這類言論并對SSRIs加以抵制時,真正需要這類藥物的人群將會陷入一個危險的境地。
事實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Moncrieff和同事的綜述文章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反思血清素假說的機會。這個源于50年前偶然提出的假說十分簡單,將抑郁癥歸于單純的血清素的影響,而隨著研究的逐漸加深,我們已經了解到抑郁癥是一類十分復雜的疾病,與很多因素有關,涉及很多的生理機制。想要探尋血清素在這種復雜的抑郁癥病理生理條件下扮演的角色,我們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而這些研究也使用到一些新技術和新方法。
除了抑郁癥本身的生理機制復雜導致其中機制難以探尋之外,血清素本身也是一個復雜的科學問題。現如今我們知道,血清素是一種復雜且多功能的神經遞質,其受體可分為七個亞科(5-HT1至 5-HT7),目前至少有十四種受體亞型已被發現,這些受體分別具有突觸前和突觸后的功能,而且還包含一個轉運體。這種復雜性賦予了它多樣的生理功能,給直接研究人類血清素的功能帶來了挑戰,需要借助先進的神經影像技術來進行研究。目前這些不同亞型受體具體的結構和功能尚未被研究清楚,更不用說研究其在如重度抑郁癥這樣的疾病中的表現。以至于在此前,人們對血清素在抑郁癥中的作用的了解幾乎完全基于間接證據。
不過,近期頻頻有好消息傳來,例如一項基于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技術的研究表明,與健康對照組相比,抑郁癥患者的血清素釋放減少。這項研究首次提供了血清素減少與抑郁癥相關的直接證據[9]。
與此同時,一系列新的工具和技術被廣泛應用起來,用于研究血清素在情緒、行為和認知調節中的作用,這些內容并未在Moncrieff等人的工作中討論。新的研究指向血清素在復雜大腦系統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些系統在重度抑郁癥中受到影響并涉及抗抑郁治療的效果[10]。雖然一些新技術,如光遺傳學,仍處于起步階段,并且依賴于動物模型,但認知神經科學已經發展出更加先進的方法,來研究血清素這類作為支撐大腦功能的關鍵神經遞質。比如有研究表明,相較于正面信息,抑郁癥患者更容易注意、理解和記住負面信息,而這種偏差與抑郁癥的易感性和維持性有關[11]。而SSRIs可以幫助扭轉這種偏差,研究表明,與安慰劑相比,接受西酞普蘭治療的患者在用藥 7 天后,對負面情緒的識別能力下降,而對正面情緒的記憶能力增強[12]。在神經層面上來解釋,SSRIs的治療可以迅速逆轉杏仁核對負面信息的過度反應,這也與這類藥物的抗抑郁作用有關[13]。因此,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待,血清素可以調節與抑郁癥相關的關鍵神經心理過程,這可能有助于解釋抗抑郁藥物治療是如何超越狹隘的神經化學焦點從而發揮作用。
人們也越來越認識到抑郁癥是當前世界上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科學家們正齊心協力確保及時發現、準確診斷和積極治療抑郁癥患者。藥物治療效果的個體性差異使得在近些年來,難治性抑郁癥(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TRD)的概念逐漸受到重視,目前對TRD的概念仍存在不同解釋,但通常認為TRD是指抑郁癥患者在接受足量足療程(至少>6周)的兩種不同作用機制的抗抑郁治療后,仍未達到臨床緩解(remission)標準的一種疾病狀態,其發生率約占抑郁癥患者的1/5[14]。對于TRD,除了傳統的更換藥物治療的方案外,科學家們也發現了新型的治療方案,比如在亞麻醉狀態下靜脈注射氯胺酮可以產生巨大而顯著快速的抗抑郁效果,在TRD患者中進行的研究也證實了這個結果,這無疑是振奮人心的好消息[15],同時也還有更多的新機制的藥物也正在被探索。有沖突并不意味著壞事,真理總是在辯論中更加清晰,科學也從來不害怕爭議,反而會在不斷的討論中找出正確的方向。起碼現在我們知道了抑郁癥的復雜性,抗抑郁藥物治療的作用也許超越了某一個狹隘的神經焦點,連接到更為廣闊的神經網絡中。想要徹底了解SSRIs的作用,或者說想要徹底了解抑郁癥,我們仍需要更多的耐心。
來自英國帝國理工大學(Imperial College London, UK)的Parastoo Hashemi相信科學家們一定能解開SSRIs之謎,她舉例說,科學家們花了80年時間才研究出阿司匹林的作用原理。“也許人們對 SSRIs 的研究過程已經失去了耐心,但這并不意味著科學界不會全力以赴繼續工作。還有很多研究人員在夜以繼日,試圖揭露其中的奧秘,也許我們現在還不具備所需的技術。但我們一定會的,一切只是時間問題。”
致謝:感謝美國Aspen Neuroscience公司的徐亦迅博士對本文的審核和修訂。

特 別 提 示
1. 進入『返樸』微信公眾號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閱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眾號,回復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獲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
版權說明:歡迎個人轉發,任何形式的媒體或機構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和摘編。轉載授權請在「返樸」微信公眾號內聯系后臺。
來源: 返樸
內容資源由項目單位提供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微博
科普中國微博

 幫助
幫助
 返樸
返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