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5日,上海浦東機場。這是中國最繁忙的民航機場之一,在平時,平均每分鐘就會有一架飛機起飛。然而今天,機場卻格外安靜。下午2點,一架機身尾部裝飾了藍色條帶涂裝,綠色尾翼的客機,緩緩滑行至跑道頭,隨著兩臺渦輪風扇發動機的轟鳴,開始向前加速。
而這正在上升的飛機,是我國最新研制的大型民航客機C919,這是他的首飛。隨著飛機一同起飛的,還有現場觀眾的熱情,其中一位白發蒼蒼西裝革履的老人,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機場上的風將他的白發吹得有些凌亂,但沒有吹干他眼眶中閃爍的淚水。一飛沖天的飛機,是他的夢想,望著振翅的銀翼,也許,他的思緒回到了七十多年前。
那時,天上飛的飛機,并不是承載夢想的天使,而是帶來死亡的惡魔。一位少年躲在田間小溝里,透過頭頂的樹枝,他看到機身上涂有紅日的飛機投下罪惡的炸彈,爆炸的巨響在四處響起。這位少年名叫程不時,此時,或許他也沒有想到,這一生,他都將與飛機為伴,將他變成承載夢想的天使。
沒有“翅膀”的“雄鷹”:中國民航業的艱難起步
時值抗日戰爭,由于日本全面占領了東南一線,抗戰幾乎所有的物資,都來自一條從印度到中國西南的航線。這條航線跨越喜馬拉雅山脈,全程需要越過崇山峻嶺,航線上下起伏,因此也被稱為駝峰航線。在這架航線上飛行的飛機,多數是運輸機,與機身上涂有紅日的飛機不同,這些飛機帶來的是抗戰勝利的希望,因此,飛機有多大,希望就有多大。
世界上最早可以盈利的民航飛機之一,正是飛過駝峰航線的DC-3,而二戰結束后,大量戰爭中使用過的DC-3涌入民航市場,讓民用航空事業蓬勃發展。飛機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讓世界變小,一條條航線有如連通世界的血管,給地球上的文明,帶來了新的活力。
新中國的民航,起源于兩航起義,1949年,舊中國最大的兩家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的員工,攜12架客機,從香港起飛,棄暗投明,加入了新中國的建設,共和國最早的民用航空事業,就此起步。從那時起,中國上空飛行的民航客機,越來越多,從活塞螺旋槳式的DC-3,CV240,到從蘇聯購買的渦輪螺旋槳飛機伊爾18,再到,從英國購買的噴氣式客機三叉戟,到70年代,中國民航各型飛機超過了100架,經營初具規模。但對于一個有960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數億人口的大國來說,這樣的規模遠遠不夠。而其中的一大制約因素就是民航飛機的研制。
二戰后,英美相繼研制了大型噴氣式民航客機,更快的速度,更舒適客艙環境,讓乘坐飛機旅行有了全新的體驗。特別是美國波音公司研制的波音707客機,設立了現代民航客機的設計模板,以至于在此之后成功的民航客機,多數都與他有類似的布局。波音707是世界上第一種在商業上取得成功的噴氣式民航客機。而商業上的成功,指的是無論是生產這種飛機的制造商,還是運營這種飛機的航空公司,都能夠通過它掙到錢。要達到這樣的目的,飛機需要有足夠的安全性與經濟性。時至今日,世界上依然有許多人認為乘坐飛機飛行并不安全,而一架經常遭遇事故的飛機,必然更會受到乘客與航空公司的嫌棄,從而斷送掉他的職業生涯。而經濟性則是商業運行的必備屬性,無論是飛機本身的成本過高,還是飛機的耗油量過大,再或是維修保養困難,在商業上都很難成功。波音707這種在當時近乎完美的民航客機,隨著中美關系的破冰,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于1972年第一次來到了中國。
中國人,也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接觸到這種先進的民航客機,而當年那位在水溝中躲避日本飛機轟炸的少年程不時,也從鋪天蓋地的報道中看到了這架飛機。此時,他已經是中國第一架噴氣式民航客機的副總設計師了。看著這架優雅甚至有些華麗的飛機,程不時的心情很復雜,作為一名飛機設計師,看到這樣的作品很難不心生喜愛。但這樣的飛機并不屬于中國人,在那個年代,中國領導人出訪,只能乘坐從國外租來的螺旋槳飛機,對此,歐洲媒體這樣評論的:“中國是一只沒有翅膀的鷹。”這讓擺在程不時眼前的工作有了更重要的意義。
夢想曾經觸手可及:運10的遺憾與ARJ-21的突破
大飛機,直接反映了一個國家民用航空工業、甚至整個工業體系的整體水平。沒有它,中國始終被西方瞧不起。
程不時和一眾航天人想啊,盼啊。終于,在1970年8月21日,國家下達文件啟動大型飛機的研制任務,“708工程”正式立項,該機被正式命名為“運10”。
那是中國首架噴氣式民航客機運十項目立項的第三年,而這架飛機也才剛剛確定它的大體樣貌,布局正是源于波音707這樣的現代噴氣式民航客機。圓柱形的機身更適應高空的座艙增壓,而將發動機吊掛在機翼下方,無論是相比三叉戟那樣的掛在尾部,還是相比像轟六那樣置于機身內部,都更有利于維修保養,這對于一架需要持續商用飛行的客機來說,更有優勢。因此,中國航空人放棄了起初在轟六的基礎上改造客機的方案,瞄準了世界最先進的水平。誰知,這一瞄就是8年時間。
那時,中國最大的飛機便是轟六,它的翼展33米,最大起飛重量79噸,而這架飛機,是對蘇聯圖16轟炸機的仿制,所有的設計均有據可循。而運十的翼展比轟六還要大10米,最大起飛重量達到110噸,在沒有任何設計資料參考的情況下,難度可想而知。從全國各地的航空設計院所匯聚而來的科研人員展開了不分晝夜的研究,繪制和發放了143000頁圖紙,終于在1980年,將我國第一架噴氣式民航客機運十送上了天。隨后,又進行了四年多的試飛,甚至7次飛抵西藏拉薩,在試飛的同時,為西藏運輸了大量物資。運-10體現出的優異飛行性能,時任波音公司總裁感嘆:你們畢業了,我們只不過比你們畢業早了幾年。而正當這架承載著全國航空人夢想與全國人民榮耀的大飛機驕傲地翱翔藍天時,項目戛然而止,運十下馬,航空人夢碎。
對于運10的下馬,有人說是缺錢,有人說是西方作梗,而如果我們翻看當時運十的設計和試飛資料后則會發現:當時該項目存在的問題中,有一項難度最大,那就是如何達到適航性要求。適航,這雖然陌生,但看起來尚容易理解的兩個字,成了捆綁中國民用飛機一道枷鎖,而這一鎖,又是二十多年。
適航,字面意思就是,適合航行。這里的航行指的是民用航線飛行。與軍用飛機不同的是,民航客機因為載客量大,航行頻繁,對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極高。美國的軍用高空高速偵察機SR-71黑鳥,在試飛以及服役過程中,因為可靠性問題摔下過三分之一,但這并不妨礙它因為出色的高空高速性能而成為一代名機,載入史冊,但麥道公司的DC-10客機,在全部的不到400架飛機里面,有15架出事,這架客機就被稱為“空難之王”以及"被詛咒的飛機",而協和客機僅僅摔了一架,就讓它退出了市場運行。民航客機對安全性的缺陷,是零容忍的。為此,民航業起步較早的國家,制定了嚴格而詳細的適航標準,大到飛機的結構強度、發動機可靠性,面對墜撞的變形、被飛鳥撞擊后的反應,小到座椅排布,應急出口位置,操縱按鈕和手柄的顏色和安全帶的尺寸,均有涉及。而適航標準中的每一條,幾乎都是來自于真實航線運輸中的事故案例。

SR-71黑鳥,配圖來自圖蟲網
可以說,西方國家是一邊摔飛機,一邊總結經驗,一邊制定了規則。這樣的規則還在不斷更新,越來越嚴格,越來越細致,民航客機的準入門檻,也越來越高。不向這個規則發起沖擊,即使造出了運十,它也永遠只能用來看,而不能投入運營。標準可以借鑒,但飛機是否符合標準,需要進行大量的試驗和試飛,但這樣的工作在運十研發的階段,并不成熟,比如運十飛行的許多參數,都沒有符合國際標準的精準可靠的測量方式,這樣原始的試飛方法和技術,并不能撐起現代客機的研制。
委屈,不甘,并沒有熄滅中國航空工程師的夢,只要一陣春風,一場春雨,這個夢就還會生長出來。
2002年,國務院立項了國產噴氣式支線客機ARJ21的研制工作,運十項目中保留下來的骨干力量,重新披掛上陣,在改革開放春風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航空人,也加入了隊伍。紅旗重新插上了陣地,新的戰斗開始了,而這一次,我們直接就瞄準了世界最先進的民機適航標準。
一架飛機是否適航,評價他的是民航管理部門,在中國,是中國民航總局,而在美國,是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這些部門會對飛機的研制生產以及試飛過程進行嚴格的監督和檢查,符合標準后,為機型發放型號合格證,型號合格證,則是一架飛機適航的標志性證件。而FAA幾乎是民用航空適航認證的鼻祖,因而在國際上具有更高的效力,取得了FAA的認證,這架客機就幾乎可以在全世界投入運營,而雖然中國民航總局對于民航客機的適航標準源于FAA,但適航取證過程尚無經驗,為此,中國與美國合作,讓FAA對中國民航總局審核ARJ-21的整個過程進行監督審查,相當于是請了一個裁判,來判斷我們自己裁判的判罰是否準確。這就是影子審查,如果通過,從此FAA就會認定中國民航總局的適航認證同樣符合他們的標準,從而不必再次進行審核,兩國相互承認對方的適航認證工作,這就是雙邊適航。
ARJ-21嘗試進行影子審查,雙邊適航,一方面可以學習西方先進的適航試飛技術,另一方面也可以為之后的客機研制奠定基礎。誰知,ARJ-21雖然是一家比較小型的支線客機,但它的試驗試飛,卻一波三折,僅僅是從首飛,到開始取證試飛,就經過了三年時間,而進入取證試飛后,更是舉步維艱,而其中遇到的最大問題,便是試驗試飛的經驗不足。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客機的試驗和試飛,是要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模擬出各種在航線運行中可能出現的異常情況,而只要是模擬,就會和現實有差距,而試驗人員要做的,就是將這種差距縮到最小,適航管理部門監督的,也是這些試驗是否能夠精確代表飛機在面對這些情況時的真實反映。例如,飛機上飛行速度儀表的指示是否準確,這需要一個校準過的,不受飛機表面氣流影響的標準量具來衡量。在之前的軍機試飛中,我們一般會在飛機前端加裝較長的空速管來測量標準的空速,這樣的方法在測量小飛機時可以避免機身對空速管的干擾,但對于大飛機來說,它的結果可能不準。
在FAA的適航試驗中,多數使用的是尾部伸出來的拖錐來測空速,這項技術,我國尚屬于空白,需要從頭開始摸索,選用甚至設計出標準的量具。中美兩國雖然簽訂了影子核查和雙邊適航協議,但或許從一開始,美國人就沒想過要讓中國這個剛轉來的新學生通過考試,對于試飛技術,依然采用封鎖的態度,我來監考,但是復習資料,你要自己解決。就這樣,從2002年立項,到2014年取得中國民航總局的型號合格證,12年的時間,ARJ21跌跌撞撞地走完了從設計到適航認證的全部過程,雖然最終因為種種原因放棄了美國的影子審查,但適航標準并沒有降低,最關鍵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航空工程師積累了適航認證經驗,是時候向更高的山峰發起沖刺了。
翱翔藍天:C919的建造歷程
事實上,早在2006年,在國家發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中,大型飛機就作為重大專項位列其中。2008年,中國成立了專門用于研制和生產大型民用客機的企業——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中國商飛這款飛機被正式命名為C-919,中國航空人心中的夢想,有了新的名字。而如果說運十是一套檢測飛機設計制造水平的測試題,ARJ-21是一套檢測民航飛機設計和試驗認證的模擬題的話,這次擺在中國航空人面前的,則是一場正考。這架飛機,不僅要符合標準,絕對安全,更重要的是,商業化運營,簡單說來,就是能夠掙錢。而此時,國際商用客機市場已經被空客和波音兩家公司所壟斷,天空中飛行的幾乎所有大型商用客機,都是這兩家公司的產品,這次中國要造的飛機,與世界上運營數量最多的中短途客機波音737以及空客A320屬于同一級別,要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必須走出一條我國從來沒有走過的道路,因此,中國商飛不僅僅要瞄準了世界先進水平,更是要留出提前量,超前于世界先進水平,這樣,才有可能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
在ARJ-21研制過程中歷練出來的航空工程師團隊,開始了新高峰的攀登。而帶領這支工程師團隊的,正是ARJ-21的第二任總設計師:吳光輝。他深切地知道,眼前的任務,不僅是一架新飛機的研制,更是對世界先進水平的一場追趕,而不進則退,是追趕中不變的真理。為了與時間賽跑,吳光輝帶領團隊實行了611和724工作制:611是指一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1小時,而在攻關的關鍵時期的724工作制,則是一周工作七天,每天24小時工作不間斷,工作人員輪流倒班休息。即使這樣,大飛機的研制難度,也超出了他們的預期。
技術方案論證,是一架飛機設計的開始,它的主要目標是確定飛機的布局外形以及主要設計參數。這些設計參數,相當于是給之后的設計制定一個目標,這個目標直接決定了產品最終的性能。C-919的技術方案論證長達半年之久,參與論證的包括全國13個省市來自航空航天、電子、冶金材料等行業以及高校的47家單位的465位專家以及20位院士組成的咨詢組,這在中國民機發展史上史無前例。
最終,C-919確定的目標是單通道150座機的中短程干線客機,基本航程4075公里,增程型能達到5555公里。同時,為了滿足市場和客戶需求,在競爭中不敗下風,這種飛機需要減小飛行阻力,減小重力,減小碳排放,在這些標準上要全面優于競品,而使用成本要減小10%以上。在適航標準上,C-919預測了國際適航標準的發展方向,設立了許多高于國際適航標準的要求,而在客戶體驗上,從方案設計階段,設計團隊就首先走訪了多家航空公司,聽取未來客戶的要求與意見。
作為C-919的首家客戶,東方航空的團隊每兩周就會抵達商飛研發中心,討論飛機的安全性、先進性、舒適性,在每一個細節給與建議,而為了更高地理解飛行,站在飛行員的角度來認識自己設計的飛機,讓飛行員愛飛,旅客愛坐,已經五十多歲的吳光輝決定開始參加飛行員培訓,并且拿到了飛行駕照。可以說,這是一架由客戶需求定制而來的商用客機。
更高的總體設計目標給各個系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滿足指標,新技術在C-919的研制過程中被大量采用。在氣動設計上,C-919采用了先進的超臨界翼型,這種機翼可以讓飛機在更高的速度下以更低的阻力飛行,即使是在十年之后,它的空氣動力效率依然可以在市場上有競爭力,而在結構設計方面,大量采用了新型的鋁鋰合金以及復合材料,減少重量。在電傳操縱系統,航電系統的選用上,也采用了世界最先進技術,而這些技術,都來自世界最頂級的制造商。
或許,當我們打開C-919的蒙皮,去欣賞它的機載系統,會看到來自世界各國制造商的商標,為此,有人會說,C-919國產的部分,僅僅是一個外殼而已。然而,我們應該清楚,商用客機的研制,與軍用飛機的思路截然不同,作為一個民用商品,商用客機最主要的任務是在運營中創造價值,為此,各國的民用飛機制造商無一例外地采用了國際合作的方式來研發和制造自己的產品,即使是在波音的飛機上,也有來自中國供應商的零件和設備,更不必提本來就是歐洲各國聯合開發的空客飛機。中國軍用大型運輸機的研制和服役已經向全球宣告了中國獨立生產制造大飛機的能力,但在商用領域,由于認證體系與使用需求的不同,在商業上,使用全國產設備,并不是最優解。來自世界各地的供應商并不能作為低估C-919設計水平的依據,反而是我國商用飛機事業與世界接軌,邁向先進水平的標志,只有這樣,C-919才能成為一款居“舉全國之力,聚全球之智”的優秀商品。正如時任波音公司副總裁說過的那樣:如果人們都可以把買來的零件組裝并飛起來,世界上就不會只有兩家大型民用飛機制造商了。
事實上,僅僅是在新型結構材料的選型和測試上,C-919所采用的材料就經過了超過2500件試驗件的試驗,逐步建立起了材料規范體系和設計性能設計數據體系,這種新材料的選用,可以使飛機相關部件減重6%以上。而正是因為新材料規范體系以及設計性能數據的精確,讓C-919的結構設計可以非常精確地進行。
全機機動平衡工況極限載荷靜力試驗是對飛機機體結構的一次大考,在這個試驗中,飛機要承受的載荷,是它在飛行中允許承受載荷的150%,而多出來的這50%,叫安全裕度。如果飛機在加載到150%載荷之前就已經出現破壞,就說明結構設計強度不足,而如果載荷遠遠超過150%但很多飛機依然沒有破壞,就說明這架飛機雖然很結實,但強度過剩,設計浪費,結構重量還可以進一步減小。2018年7月12日下午,在民航總局代表的見證下,C-919上了地面試驗臺,60%……80%……100%……150%,保載三秒,三,二,一。C-919順利通過了最大載荷測試,結構強度符合要求,而在后面的靜力破壞試驗中,C-919在載荷達到160%時出現結構破壞,完全符合設計時的計算,精確的結構計算,是大飛機設計的基礎,這也體現出了我國強大的飛機設計能力。而在飛機設計中,這樣的試驗與計算只是冰山一角,而即使是國外供應商的產品,也需要商飛提出精確而合理的需求,與飛機系統緊密集成,有機融合,而這些工作當中,很多都是我國首次進行。

2011年,C919,配圖來自圖蟲網
在2017年5月5日,C-919首飛成功,而白發蒼蒼的程不時,此時是C-919的名譽總設計師,中國商飛的飛機設計顧問組成員。面對騰空而起的大飛機,相信他也知道,首飛只是開始,更大的考驗,還在后面。除了前面所說的結構試驗之外,還有幾百個適航驗證試驗和試飛項目需要進行。當年的ARJ-21,用了300項試驗,528個試飛科目,2942個起降架次以及5257小時的飛行,才完成了適航驗證,更大、更復雜、更先進的C-919,必將面臨新的挑戰。
失速、最小離地速度以及自然結冰試驗,被稱作C-919取證試飛中的“三大戰役”。失速是民用飛機飛行員在飛行中不可觸碰的禁區,一旦飛入深度失速狀態,飛機將會失控,難以改出,最終機毀人亡,而失速試飛,則需要試飛員在飛機失速狀態的邊界不斷試探,在不同的速度以及迎角下,試驗出這架飛機的失速邊界,這條邊界就像是一條紅線,未來會畫在飛行員的飛行手冊上,讓飛行員遠離。失速傘是試飛飛機一旦進入深度失速狀態失控之后,把飛機拉回來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這項技術,過去在我國是空白,而在C-919的試飛中,我國首次完成了這項技術的試飛,為之后對禁區的試探,提供了保障,而優異大坡度的滾轉性能,也是飛機能夠從失速狀態改出的重要條件,通常,民航客機的滾轉坡度不會超過60度,而在C-919的試飛中,這一數據達到了105度。在飛機機翼完全垂直于地面的狀態下,依然可控,這也為試飛員帶來了十足的信心。
最小離地速度試驗,則是要測試飛機能夠離地的最小速度,為了試驗出這種速度,飛機必須在最大的抬頭姿態下在地面滑行,此時,飛機的尾部會與地面摩擦。為了試驗這項性能,需要在機尾加裝防止損傷的尾橇。試飛員則需要輕柔地將飛機機頭抬起,保持尾橇擦地,在幾乎看不見跑道的情況下保持飛機姿態穩定,獲取飛行數據。若機頭抬得過高,尾橇也無法保護飛機,結構將會損壞,而如果抬頭不夠,尾橇接觸不到地面,則無法獲取精確的數據。隨著尾橇與地面接觸摩擦出的一路火花,這項試驗被試飛團隊攻克,C-919獲取了精確的最小離地速度,為以后的安全運行,又畫出了一條精準的邊界。
2006年,一架空警200在安徽失事,機上除了機組成員之外,還有34名中國最頂級的預警機領域技術人員,其中還包括兩名將軍,而這慘烈的事故,正是源自于機翼結冰。在溫度極低,濕度較高的區域飛行,水蒸氣會在機翼表面凍結,結成的冰雖然肉眼看起來不起眼,卻會給飛機的氣動外形帶來極大的影響,導致升力驟降,阻力上升,引發事故。而自然結冰試驗,則是要專門尋找這樣的環境,來測試飛機在結冰條件下的飛行性能,以及飛機上的除防冰設備,能否抵御這樣的結冰環境。
在ARJ-21的試飛中,為了尋找合適的結冰環境,它甚至專門飛到了北美的五大湖地區。然而,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難道在這么大的國土面積上,就找不出一塊兒適合做結冰試驗的天空?2020年12月,在航空工業試飛中心的帶領下,中國航空人吹響了C-919自然結冰試飛攻堅的號角。在航空學與氣象學交會的領域,專家學者專門使用氣象飛機,在全國范圍尋找結冰環境,初步掌握了陜西、新疆地區以及周邊省份的結冰資源,形成了結冰預測,結冰氣象實時檢測方法,建立了結冰資源數據庫,沒錯,在平時航行中飛機避猶不及的環境,在試飛中反而成了一種資源。
終于,在2022年,飛機全面完成了自然結冰試驗,在飛機縫翼處,如愿看到了三英寸厚的冰,并且記錄下了飛機除冰裝置開啟后結冰脫落的全過程。杜毅潔是參與飛機結冰試驗的飛行工程師之一,在飛機降落后,機頭上依然有一大塊冰,機務將它清理掉,掉在地上,摔成了好幾塊,杜毅潔撿起一塊,帶回了家,送給了她的兒子。在朋友圈里,她的兒子捧著那塊冰,笑容燦爛,但仿佛又不能完全理解此中深意。而杜毅潔寫道,一個出晚歸媽媽回家給孩子的禮物,是機頭上掉下來的一塊冰。沒錯,這塊冰,是中國航空人的勇敢、智慧與勤勞凝結而成的,是最好的禮物。
顫振、空速校準、載荷、操穩特性、高溫高寒試驗試飛,閃電間接效應試驗,濺水試驗,全機應急撤離演示試驗,C-919順利完成了729個科目的試飛,2022年9月,完成了全部適航審定工作,獲得了中國民用航空局頒發的型號合格證,并于2022年底交付給中國東方航空。中國的旅客人,即將能夠乘坐自己的大飛機,遨游天際。
伴隨著C919上天,與喝彩相伴的,還有很多爭議。
“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不是全國產,不如不造”……諸如此類的說法,在網絡上流傳甚廣。但他們忽視了C919將帶來的重大改變。
曾經,中國大飛機研制停擺的幾十年里,美歐的飛機趁機擠滿了中國的藍天,賺得盆滿缽滿。我們都聽過那個“出口10億雙襪子換一架飛機”的典故,但與之相對的美國故事,卻是“出口一架波音747,可以抹平進口12000輛汽車造成的貿易逆差”。
據中國商飛統計,2021年,全球共有20563架客機,其中中國機隊3695架,占比18%。這個比例在未來200年可能提升至21.1%!
需求大,生產薄弱,勢必會帶來巨大的采購成本!
買飛機不是買白菜,如果數以千億計的采購訂單,哪怕只有一部分轉入國內,能拉動多少內需?創造多少就業崗位?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我國目前還不具備生產部分關鍵部件的能力,比如發動機。但先有了大飛機,才有了平臺,才有了需求,才能帶動民航發動機產業的發展。
以前,我們用外國制造商的飛機,處處受制于人。飛機上一個燈泡壞了,廠家讓你換整個組件,你只能忍氣吞聲。中國生產不了發動機,連一個燈泡都不會生產嗎?并非如此,這就是壟斷,飛機制造商可以用安全性為由拒絕中國企業生產的任何部件裝上飛機。但現在,我們自己作為制造商,擁有了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大飛機,且通過了適航認證,我們就有權決定部件許可生產,這將打破歐美長期以來的壟斷,逐漸構筑中國航空工業自己的產業鏈。
更關鍵的是,C919的成功意味著中國航空工業的重大進步,必將吸引越來越多的學子投身到航空專業當中,我們的航空人才不用再擔心斷檔,不用再擔心人手不足,這才是中國航空工業未來繼續騰飛的基礎!
C919的問世,不僅是功在當代,更是利在千秋!一定會有會有越來越多的國產飛機翱翔于天際;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堅定、且自信地投身于中國航空事業;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坐上我們自己的大飛機,行遍祖國的大好河山,踏遍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C919只是一個開始,中國航空事業的偉大騰飛,不知道還要過多少難關,不知道還要面對多少質疑,不知道還要投入多少人的青春與熱血……但我們堅信,這個偉大目標終有一日,能夠實現!
在中國商飛制造基地,停放著一架運10的樣機,在樣機旁邊的紅色石碑上,刻著四個大字。那正是數十年來,幾代航空人傳承至今的堅定信念——永不放棄!
今年,程不時老先生已經93歲高齡了。也許,程不時老人也會乘坐這架他熟悉的飛機,遨游天際。這片天空,依然是幾十年前他透過樹枝遙望的那片,但這片天空下的世界,卻是一個新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他的心愛之物,他的希望所寄,會將萬千百姓的幸福,帶向四方,讓人與人的心貼的更近,讓這個世界,更加美好。
本文為科普中國·星空計劃扶持作品
作者:茍勝老師
審核:戴玉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飛機系教授)
出品:中國科協科普部
監制: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星河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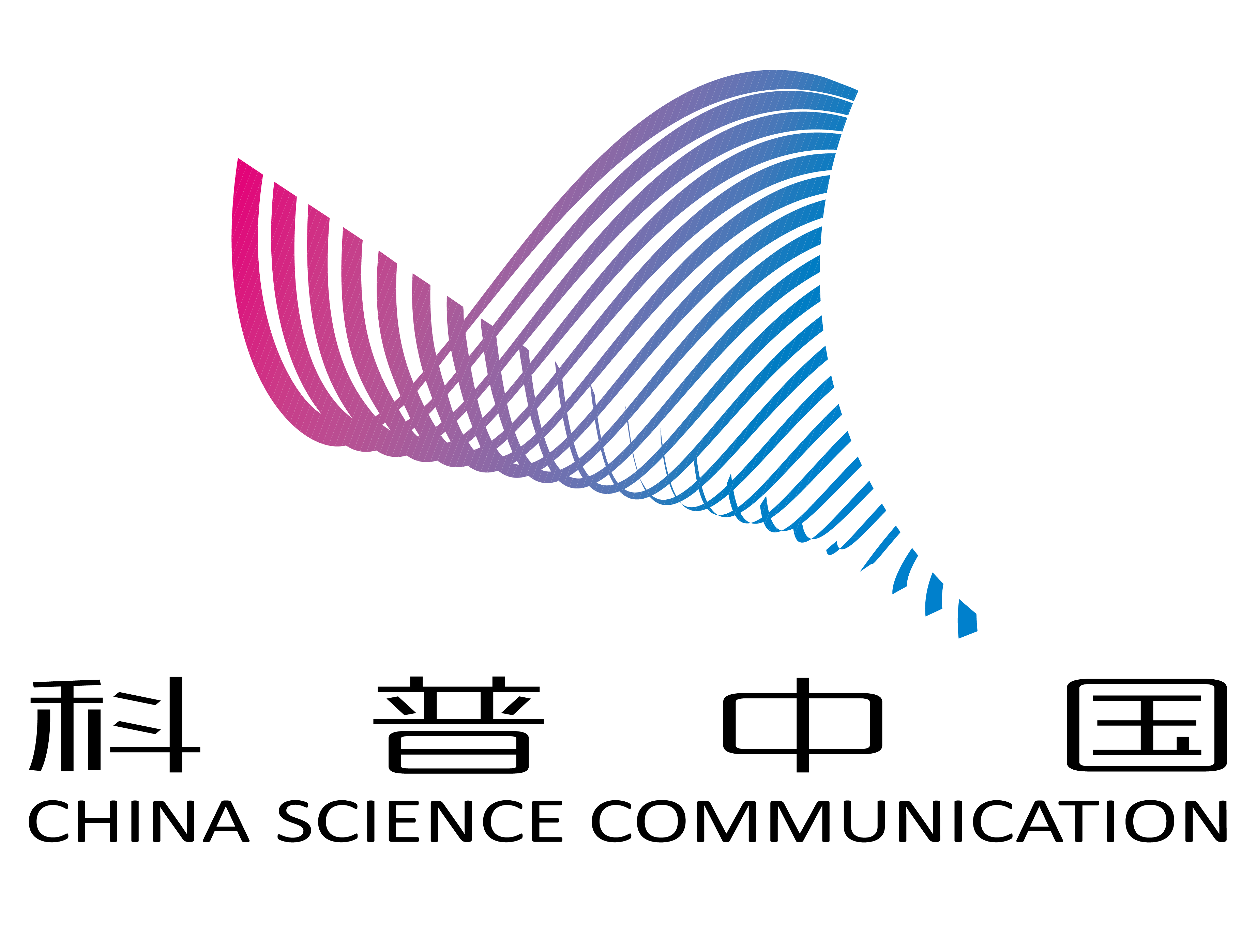
來源: 星空計劃
內容資源由項目單位提供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微博
科普中國微博

 幫助
幫助
 科普中國創作培育計劃
科普中國創作培育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