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一張照片,點擊發送按鈕,短短幾秒鐘,一張圖片在量子光的運載下穿過長達100公里的光纖,完成信息的安全傳輸。100公里,國際上最長的量子直接通信距離紀錄就誕生在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
5年來,量子院作為本市首批支持建設的新型研發機構之一,已孕育出一系列世界級科研成果。打破科研單位之間、學科之間、科研與產業之間的“三堵墻”,新型研發機構以開放創新的大膽探索,集聚全國乃至全球頂尖人才的聰明智慧,在重大基礎前沿科學研究、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方面接連取得突破性進展。

阻止“竊聽風云”
量子直接通信距離創世界紀錄
告別竊聽風云,量子通信因極高的安全性而成為科學研究的前沿領域之一。202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發給了量子信息領域的三位科學家,進一步引發全球對量子科技的高度關注。
北京在量子研究領域優勢明顯。早在2000年,清華大學教授龍桂魯就帶領團隊提出了量子直接通信理論。“利用量子態的特性,我們可以在信息傳遞時邊檢查、邊通信。暗中竊聽會引發量子態的狀態改變,對方既不能隱藏竊聽行為,也無法竊取任何信息。”龍桂魯解釋,量子直接通信將傳統保密通信的密鑰分發和密文傳輸雙信道結構,改變為單信道結構,**不僅能夠感知竊聽,還能夠阻止竊聽。**不過,當2016年龍桂魯帶領團隊啟動量子直接通信原理樣機的研制時,工程化實踐的短板制約凸顯出來。“高校科研小團隊的力量遠遠不夠。你很難要求物理系的學生通曉電子、半導體、軟件編碼等技術,所以初始產品里藏著一些小問題,影響了優化升級的腳步。”這也折射出當時北京量子研究的不足:中科院、北大、清華等高校院所爭相發力,但科研力量分散,資源優勢并未有效轉化為競爭優勢。2017年12月24日,由北京市政府發起,聯合多家頂尖學術單位共同建設的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揭牌成立。作為北京首批新型研發機構之一,量子院邁出了先行先試的步伐,大力引進全球量子科技領域人才的同時,還組建起一支高水平工程師組成的技術保障團隊,打造產學研全鏈條暢通的科研平臺。2019年,龍桂魯以“雙聘制”形式加入量子院,擔任該院副院長。在這里,財政科研經費實行“負面清單”,設備采購能“一鍵下單”,研究團隊充分感受到新機制下科研進展的“日新月異”。隨著軟硬件工程師陸續加入團隊,新一代樣機在設計上更加成熟。
在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的實驗室里,龍桂魯教授與研究人員正在進行量子直接通信樣機研發。本報記者 和冠欣攝
整合資源協同創新,**龍桂魯團隊在量子院接連取得突破性成果:**2020年成功推出世界首臺實用化量子直接通信樣機,率先實現10公里光纖鏈路每秒4千比特通信速率的量子保密通話;同年,通過編碼優化,直接通信距離提升至18公里;**2022年,龍桂魯團隊和清華大學教授陸建華團隊合作,設計出相位量子態與時間戳量子態混合編碼的新系統,將量子直接通信距離一舉刷新至100公里,創下世界紀錄。**這意味著,依靠現有的成熟技術手段,城市之間已能實現點對點的量子直接通信。接打量子電話
將在3至5年內實現
基礎研究科研周期長、投入大、轉化難,科研人員往往要坐“冷板凳”。但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吸引科研人員不斷深入前沿領域。**“一個科學發現到底‘有沒有用’,我們無法預計,但如果不去做,就只能永遠跟在別人的后面。”**中科院物理所懷柔研究部主任呂力表示,沒有基礎研究的進步,就沒有人類文明的進步。量子理論誕生在百余年前,第一次量子革命催生了現代信息技術。而利用量子的特性推動量子通信等領域走向產業化,便是正在進行的第二次量子革命的目標。“量子技術是從基礎研究到應用轉化最快的領域之一,量子院正是用靈活的體制機制打通了瓶頸,推動基礎研究的成果向產品化應用轉化。”龍桂魯說。從實驗室到產品的路注定不會一帆風順。在測試新一代量子直接通信樣機時,信號怎么也無法接通。為了找到故障點,團隊頗費了一番工夫,花費數月排查了數百個零部件,迷霧終于被撥開——**兩條光纖在對接時出現了誤差,雖然誤差不過毫厘,卻導致光路中斷。**工程師仔細調整后再測試,通了!現在,第二代量子直接通信樣機的通信速率達到了每秒千比特的量級,能夠穩定實現圖文傳輸,并且已從“一對一”通信發展到了多人“群聊”,初步構建起了量子直接通信網絡。
 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超導量子計算實驗室內,研究員正在進行科研工作。本報記者 和冠欣攝
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超導量子計算實驗室內,研究員正在進行科研工作。本報記者 和冠欣攝
“在量子院做科研,很舒心。”工程師宋嘯天去年加入了龍桂魯團隊,最近,他正向新一代量子直接通信系統的芯片發起挑戰。上個月,他還在為芯片過高的誤碼率苦惱,通過反復摸索、嘗試,終于有了新突破——通過對關鍵部件重新設計,芯片誤碼率降至3%,整體結構也更加緊湊小巧。近期,龍桂魯要把量子直接通信技術帶出實驗室,利用已鋪設的光纖網絡進行測試。“我們要讓技術在真實環境中接受考驗,再做進一步優化。”**龍桂魯預計,3至5年內,量子直接通信網絡將真正走入人們的生活,接打“量子電話”、發送“量子信息”將可觸可及。**北京“四不像”研究所的
創新“超能力”
與龍桂魯相似,陸續加入量子院的頂尖人才紛紛感受到北京推進前沿創新的加速度。2019年,長期從事超導量子計算和量子模擬研究的于海峰入職量子院。他快速組建起具有物理、電子、計算機等不同專業背景的40余人科研團隊,圍繞建造實用化量子計算機的總目標發起攻關。同年,32歲的常凱在馬克斯普朗克微結構物理研究所完成博士后研究,雖然沒有知名頭銜,量子院依然看到了他的科研潛質。在加入量子院并組建低維量子材料團隊后,短短2年時間,他的研究成果就登上了《科學》雜志。“量子院對于青年科學家的科研經費支持力度,讓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設想去建設世界一流的實驗室,不必因為經費問題而做出種種妥協。”常凱說。以研發高速光纖量子密鑰系統而聞名的袁之良在2021年歸國,擔任量子院首席科學家。量子院對其科研支持工作的開展,以天為單位計算。從簽訂聘用合同到在崗投入科研,**短短4個月的時間里,他所需要的科研設備論證、300平方米實驗室改造、科研團隊組建工作全部完成。****新的運行體制、新的財政支持政策、新的績效評價機制、新的知識產權激勵、新的固定資產管理方式,**量子院不斷釋放創新活力,新的世界紀錄在這里不斷誕生。
 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科研人員正在量子計算裝置下全力攻關。本報記者 和冠欣攝
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科研人員正在量子計算裝置下全力攻關。本報記者 和冠欣攝
2021年中關村論壇上,于海峰團隊的重磅研究成果發布——長壽命超導量子比特芯片突破500微秒大關,標志著我國在超導量子芯片研究領域走到了世界前列。今年3月,袁之良團隊的實驗室發布最新成果,在世界上首創開放式架構雙場量子密鑰分發系統,完成615公里光纖量子密鑰分發實驗。這種開放式架構設計簡潔,能極大節約量子網絡系統的建設成本,助力未來實現在城市間撥打“量子語音電話”。“不完全像大學、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業,不完全像事業單位”,不少科研人員將新型研發機構親切地稱為**“四不像”單位**。正是這種“四不像”的探索,打破了基礎研究與產業的隔膜,成功激發和凝聚科學家精神,讓北京原始創新和前沿探索呈現出“千里馬”競相奔騰的蓬勃生機。
來源: 北京日報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微博
科普中國微博

 幫助
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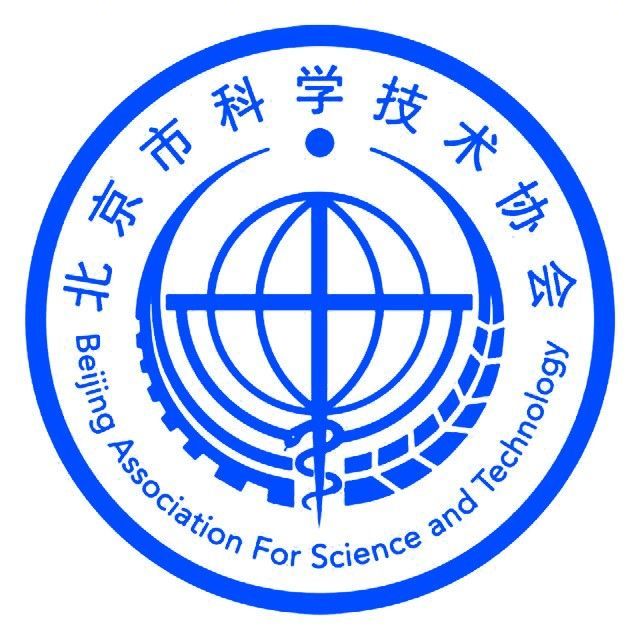 北京科協
北京科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