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0年以后,中國歷史上兩個帶南字頭的政權(quán),一個是南宋,一個便是南明。前者在各類戲劇作品中幾乎就是昏君奸臣的代名詞,可是這樣的南宋,居然從1127年撐到了1279年,陸續(xù)面對女真、蒙古兩大強敵,可以說是當(dāng)時文明國家中抵抗得最久的一個。
那么南明呢?同樣是舊都被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攻破,為什么南明就不能像南宋那樣撐150年,為傳統(tǒng)華夏文明留下一脈傳承呢?

最近在看顧誠先生的《南明史》,腦子里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今天一起來聊聊看。
滿清入關(guān)之際,不超過十二萬軍隊,而明朝在南方的總兵力,將近百萬人。更何況南方本身人口數(shù)就多于北方,經(jīng)濟也遠(yuǎn)較北方發(fā)達,南明政權(quán)為什么就不能將南方雄厚的經(jīng)濟實力和人口優(yōu)勢,轉(zhuǎn)化為抵御滿清的堅實力量呢?再加上大順和大西兩支農(nóng)民軍的余部,以及鄭成功父子的海上部隊,這三股力量如果能放棄往日恩怨,團結(jié)一起一致對外,獲得全面勝利將清廷趕出山海關(guān)或許有些困難,但保住半壁江山,你說會很難么?

問題就在于,南明做不到團結(jié)二字。
首先是南明政權(quán)本身,弘光帝立國僅一年,就連續(xù)發(fā)生了三樁大案,第一樁,是和尚大悲自稱原是明朝親王;第二樁,則是某官員的仆人遇到一少年,內(nèi)衣織有龍紋,驚問其身分,少年自稱是崇禎皇帝的皇太子;第三樁,是一個女人跑到南京,說自己是福王即弘光帝的元配正妃。
結(jié)果這三個人,不論親王、太子、王妃,朝野議論紛紛,南明當(dāng)局卻都指為虛妄。這背后,顯然是眾人對南明本身的不滿所致,南明弘光帝,一當(dāng)上皇帝,就沉湎于酒色之中。掌權(quán)的馬士英、阮大鋮,也是個個醉生夢死,利用手中的權(quán)力鬻官肥家。阮大鋮甚至公然以行賄作為理財妙方。這樣的朝廷,如何能讓百姓放心?讓北邊的滿清不看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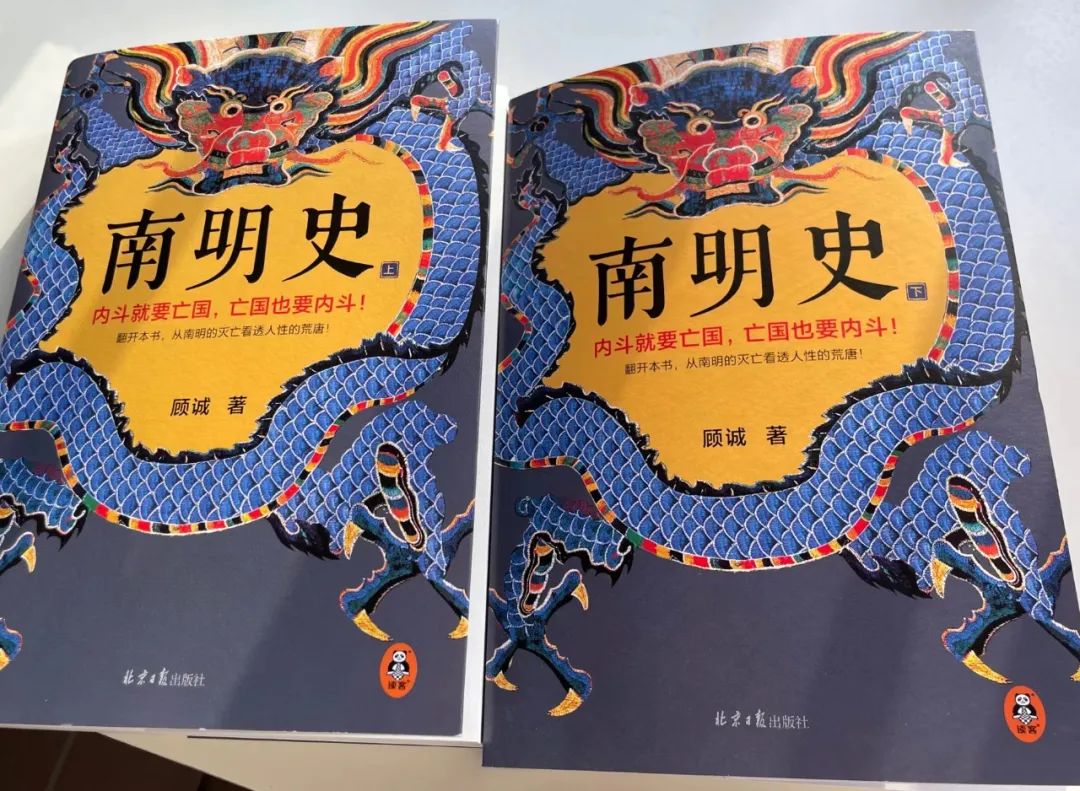
另一方面,南明朝廷對整體局勢的判斷,也出現(xiàn)了極大的錯誤,此時吳三桂已經(jīng)投降清朝,做了平西王,可是馬士英這些人,居然還以為是吳三桂借清兵擊敗了“闖賊”(就好像唐朝借回紇兵平定安史之亂),個個興高采烈,即決定“封關(guān)門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誥券、祿米,發(fā)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赍送”。
而在滿清奪取天下的意圖完全暴露之后,南明依舊有聯(lián)合李自成、張獻忠余部一起抗清的操作空間。在另一邊,張獻忠余部李定國也有意歸順,1647年,大西軍進入云南,與沐天波(即金庸小說里的沐王爺)達成合作,打出了“共襄勤王,恢復(fù)大明天下”的旗號。
但問題是南明太不爭氣,清兵尚未南下,自己先鬧起了內(nèi)訌,武昌的左良玉宣布要清君側(cè),順長江東下,發(fā)布檄文討伐馬士英,結(jié)果船到九江,他一口老血噴出來,死了。兒子左夢庚,一轉(zhuǎn)身便降了大清。

這樣一來,南明所謂的江北四鎮(zhèn)便亂了套,沒多久徐州、揚州、南京都被攻克,弘光帝在位僅一年就被送往南京處死。
到了這步田地,南方各君該覺悟自省,團結(jié)一致了吧?偏不!反而拉開了一場更大內(nèi)訌的序幕,杭州的潞王、撫州的益王、桂林的靖江王,一個各跳出來爭搶監(jiān)國的頭銜,其中又以福州的唐王和紹興的魯王最有實力,但這個時候,你的實力應(yīng)該拿出來對付滿清對不對,當(dāng)時清朝正在推行薙發(fā)令,江南一帶反清風(fēng)潮不斷,可是南明的這些王爺,沒有一個爭氣的,只知為了彼此的地位而搶個你死我活。
這一點,金庸小說《鹿鼎記》都提到了——天地會和沐王府都說要反清復(fù)明,但復(fù)的是哪一個明又有講究,天地會隸屬于延平郡王府,擁立唐王;沐王府則擁立桂王,即永歷帝朱由榔。結(jié)果因為擁唐還是擁桂,雙方成員因此而大打出手,甚至還鬧出了人命。

這當(dāng)然是文學(xué)描寫,可是背后卻是真實的歷史。隆武帝(唐王)就是在這樣的邏輯之下,與魯王形同水火,爭斗不斷,結(jié)果不能形成合力,被清軍各個擊破。最終便是1659年永歷帝逃入緬甸并遇害。
(聲明:本文來源地圖帝,轉(zhuǎn)載僅做學(xué)習(xí)交流,非商業(yè)用途,所有轉(zhuǎn)載文章都會注明來源,如文章、照片的原作者有異議,請于后臺聯(lián)系我們,我們會進行快速處理或刪除,謝謝支持。)
來源: 地圖帝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公眾號
 科普中國微博
科普中國微博

 幫助
幫助
 寧夏搭搭樂樂
寧夏搭搭樂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