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個(gè)民族、一個(gè)國(guó)家的靈魂,而典籍則是文化傳承重要的物質(zhì)載體。《文脈華章——冀藏古籍文化展》于2025年6月26日在河北博物院開(kāi)展,168種各類古籍吸引了大批觀眾的目光。河博社會(huì)教育人員精心設(shè)計(jì)了“開(kāi)卷有益 古籍新知”系列教育項(xiàng)目,包含線下活動(dòng)與線上課程。我們常說(shuō)一句話,叫做“有錯(cuò)就改”,用《論語(yǔ)·學(xué)而》中孔子的原話說(shuō),就是“過(guò)則勿憚改”。那么,古人要怎么改正書(shū)寫時(shí)犯的錯(cuò)誤呢?今天咱們就從一件小小的文物——書(shū)刀談起。
大家知道,長(zhǎng)而窄的竹片或木片叫做簡(jiǎn),較寬的叫做牘。當(dāng)紙張還沒(méi)有普及之時(shí),人們把簡(jiǎn)牘用繩子編連成冊(cè),這就是早期的書(shū)籍形式。而書(shū)刀,就是古人專門用來(lái)削刪簡(jiǎn)牘中文字的小刀。請(qǐng)看漢字中刪除的“刪”,其左邊是用簡(jiǎn)牘編成的“冊(cè)”,右邊就是一把刀。漢代之前的古人管它叫做“削”,漢代人稱為書(shū)刀。當(dāng)不慎出現(xiàn)了刻寫或書(shū)寫錯(cuò)誤時(shí),古人會(huì)用書(shū)刀將錯(cuò)寫的字跡、墨痕刮干凈。另外,竹木簡(jiǎn)牘制作起來(lái)不容易,因此古人很珍惜它們,有時(shí)也會(huì)把用過(guò)的簡(jiǎn)牘重新削干凈,去除上面的墨跡,重復(fù)使用,所以,書(shū)刀可以算是“古代的橡皮擦、涂改液”了吧。
根據(jù)滿城漢墓考古發(fā)掘親歷者盧兆蔭先生記述,劉勝墓金縷玉衣腰部左側(cè)放置鐵刀一把,這把鐵刀有環(huán)首及錯(cuò)金紋飾,是為刊削簡(jiǎn)牘用的;竇綰墓鑲玉漆棺內(nèi)也出土了鐵書(shū)刀,其制作精致,形體較小,共四十七件,分為兩束,長(zhǎng)度為15-18厘米,裝飾考究;此外,竇綰漆奩內(nèi)也放置了一束鐵書(shū)刀。由古人“事死如事生”的喪葬觀念推斷,這些出土?xí)稇?yīng)該是劉勝夫婦生前使用或喜愛(ài)之物,因此才會(huì)隨葬。中山靖王劉勝有作品《文木賦》和《聞樂(lè)對(duì)》傳世,由這些出土的書(shū)刀,我們可以推想,他們夫婦二人或許都有一定的文學(xué)造詣吧。

滿城漢墓出土銅書(shū)刀
剛才提到,書(shū)刀還有一個(gè)名字叫做“削”,我們今天的一些詞語(yǔ),都是從“削”衍生而來(lái)的。比如,人們?cè)谡?qǐng)他人審讀、指正自己的文章時(shí),會(huì)使用“斧削”一詞;古代官員在寫奏折時(shí)先寫個(gè)草稿,在正式呈上奏折后,便將草稿銷毀,稱之為“削草”;到了唐代,紙已普遍使用,盡管不再用簡(jiǎn)牘,但文人們追求風(fēng)雅,懷念古風(fēng),于是稱廢棄的草稿為“削稿”,等等。
“南陽(yáng)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千古名篇《陋室銘》中提到的“子云”,是漢代思想家、辭賦家揚(yáng)雄的字。揚(yáng)雄在《答劉歆書(shū)》一文中提到了一句話:“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shū)也”。后人由此總結(jié)出一個(gè)成語(yǔ),叫“不刊之論”,這里的“刊”,指的是“刊削”,也就是用書(shū)刀刮去錯(cuò)字之意。“不刊之論”,指的是不能改動(dòng)或不可磨滅的言論,用來(lái)形容文章或者言辭的精準(zhǔn)得當(dāng)、無(wú)懈可擊。
古代辦理文書(shū)、管理案牘的書(shū)吏們,是最離不開(kāi)刀筆的,而使用筆和書(shū)刀也是書(shū)吏的專長(zhǎng),所以他們被稱作“刀筆吏”。即使在普遍用紙的年代,這個(gè)代稱也依舊流傳。后來(lái),代替不識(shí)字的人書(shū)寫信件與狀紙的訟師,也被稱為“刀筆先生”。您可別小瞧這小小一把書(shū)刀,它也是中國(guó)古代文化傳承的助力者和見(jiàn)證者呢。

滿城漢墓出土鐵書(shū)刀
開(kāi)卷有益,古籍新知。本期線上課程就與您分享這么多吧,咱們下期不見(jiàn)不散。
來(lái)源: 河北博物院


 科普中國(guó)公眾號(hào)
科普中國(guó)公眾號(hào)
 科普中國(guó)微博
科普中國(guó)微博

 幫助
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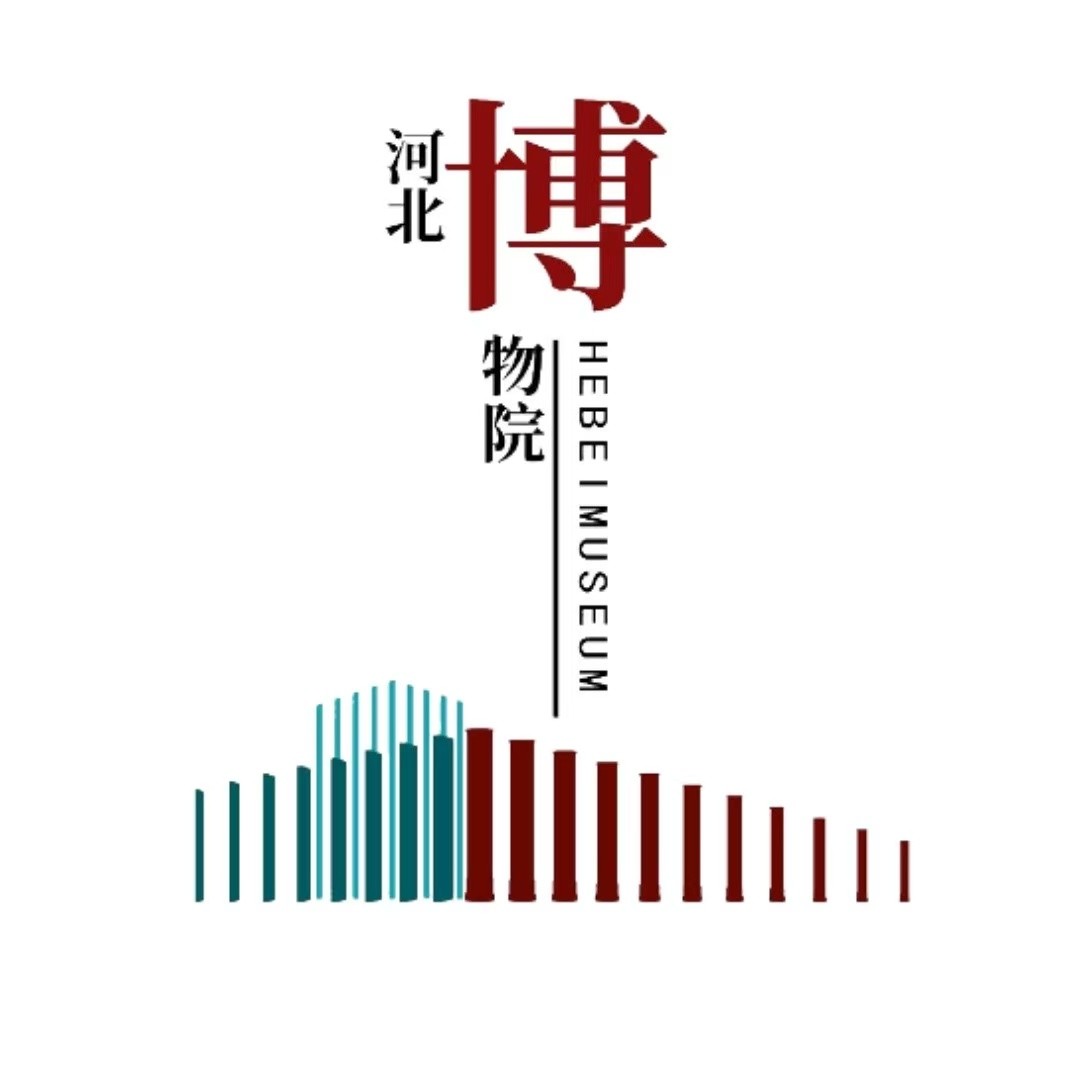 河北博物院
河北博物院 
